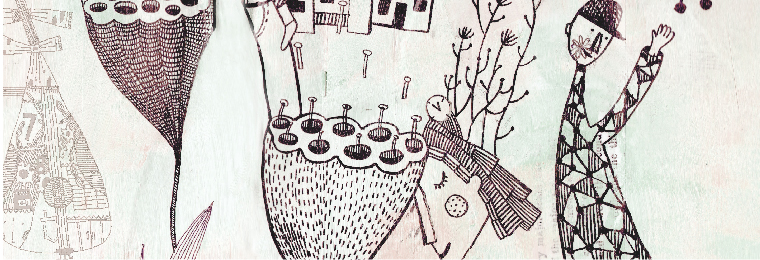梳声音︱ 被声音埋没之前
|
首頁︱鏡像︱購買出版品 |
|
一直都习惯将折这个字写成繁体字‘摺’。觉得简体字的折太像拆了,老是怀疑自己写错。繁体版的折右上角有个羽,下面有个白。我不懂这字原本的意思有没有白色羽绒被被折叠起来的意象,繁体的折让人联想到安静、洁白、温暖、静止、 沉淀着的时光。
可是我对‘折’这个动作的回忆,却不是那么美丽。
中学的时候,家里为了多赚一些钱来维持开支,全家总动员地接了折卡片的家庭工业。每逢新年、圣诞节前便是我们一家大小开始忙碌的日子。一栋一栋如柱子般的贺年卡和大小纸箱在家里的各个角落叠着,比我们高。年尾的时候家里到处可见各种不同的‘春’、‘贺’等烫金字样。有好几年马来新年和华人新年很接近,所以家里堆的贺年卡红一边,青一边。将近十月左右则是银色白色青色的圣诞树图样。在八月左右,则是紫色和烫满金色的卡片。每一年看着这些刚从印刷厂搬运过来时还未撕成一张一张单位的卡片,有新书混着廉价香精的气味,仿佛提早感受着那似乎存在的季节变化。看着这些卡片堆叠成的柱子,都在心里想着,今天要完成几根柱子呢?
我们必须先将这些卡片一组一组地拆下来,把不是属于卡片的白色边框和卡片分开。然后从撕开的方形洞处将卡片一叠一叠地拔出来。这样撕开的时候,很容易被锐利的纸张割伤手指或手臂。记得空中总有白色细碎纸屑飘扬着。天窗亮着的时候,细微的小点在阳光中缓缓浮起又飘落着。我们总是用眼尾瞄着墙壁上的钟。桌上和地上慢慢地累积着一层灰白色橡皮擦末般的纸屑和金银粉末。
父亲最常担任的工作通常是擀内页和卡片。为了要使折痕看起来工整,父亲有一根他特有的铁棒。其中一人必须帮忙把纸张大略的半折(但是没有折痕)。 二三十张纸张卷成一半叠着一手捏着一边,看起来像孔雀开屏般。对齐一边后父亲的铁棒便会像擀面般擀过这一叠纸,铁棍所压过的地方,一叠内页纸(或卡片)就会有一条清晰的折痕。
数算卡片是我最擅长也最常被分配的任务。首先,将用左右手将一叠卡片掰开(和老师们分油印考卷时的动作一样)。之后,右边这一边就会出现数十或数百条细线。拇指辨认着五这个分量的宽度和间隔距离。每五个空隙便按一次。心里数着五、十、十五。就一叠。习惯看这样的细线空隙后,空隙就尽可能越密越好,因为会比较快。我长期这样五、十、十五地算着。到最后已经不是在看线条数算了而是记着‘五’的触感和空间。只要集中于记着那个属于‘五’的触感,就可以一边看电视节目一边数卡片了。
那时放学回家放下书包吃完饭,别人在客厅围坐着追看港剧的时候,便是我们开工折卡片的时候了。电视也许是开着,却也不太看。用耳朵听的较多。啊今天谁跟谁在一起,谁又出卖谁,谁其实是卧底。那段折卡的日子大都夹杂着如节拍器一般精准规律的铁棍擀纸声。
回想起折卡的日子,先想起的就是这个声音。空隆空隆。空洞又呆板地重复着,那是父亲擀纸张的声音。顺序想起的便是钟声。嘀嗒嘀嗒。港剧对白和后巷那家人骂小孩催促小孩吃饭的叫骂声。想起了声音之后,便是画面:那些折好一叠叠整齐排放好的卡片和纸箱;烫金的Season's Greeting字样和其虚拟的季节感;die-cut出来的圣诞树或雪花、麋鹿的图样掉满桌底,堆积成小山;贴满价钱贴纸的桌子边缘;滑溜溜的透明塑胶袋叠不起来而在某一天下午毫无预警地倒塌等等。
又是九、十月了。如果贺卡工业还是很兴旺,如果我们家还在继续着折贺卡的家庭工业,现在应该已经进入折卡旺季了。那些年和那些似乎存在的季节如今已经渐渐淡去或以更虚拟的方式替代着季节的运转。而这些提早来的季节气氛终究不再堆积在我们家了。
往后的日子,不再需要日日数算卡片、贴内页、标价贴纸了。若在信箱里发现粉红色、白色和米色的信封再加上别人的字迹时,便会想起那些提早被运来、充塞家里每一个角落--属于节庆的香气。这些象征性的香气虽然多年来一直不被我接受和喜欢。可是,这些我不喜欢的人造香气和工厂运作般重复数算卡片的日子,已经足以构成一段特殊的时光。甚至已经很诡异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暗中堆叠成我对‘家’的记忆了。
犹如那些十月、十一月开始堆满桌脚的白色麋鹿。
[ 點閱次數:6295 ]
4 則回應
我也折过我也折过
不过只是很短的一段日子
在外婆家,通常是下午,电视同样是听着
折折折折折折折.....
偶尔谁不小心走过或者不小心根基排得不稳
好不容易排起来的塔就在惊呼声中倒下
收拾好之后又继续安静的折。
全部都折好包装好之后排在客厅一角等着被送走。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壮观。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家任何一个小孩帮忙都可以拿工资啊。大概那是我第一份薪水啦。(居然忘记被分到多少了)
真是叫人想念的沉默和专心啊。
找到知音人了。
啊!我折了蛮多年。折折折折折折折。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每天爸爸说,今天,我们的目标是XX张。然后时钟就开始滴滴答答。脑子里空着。只是。五。十。十五。横。五。十。十五。竖。要十字排着才不会乱。
那些一包一包的橡皮筋。脚下粉粉的触觉。呼吸中总感觉鼻子有小粉屑。时钟。还没到。搬。抬。扛。粘。对齐。
两分钱一张。白板上写着的数目字。。。
真是让人想念的沉默与专心啊。
寫下你的回應
請用以下一項機制登入或註冊:
- » 使用Facebook帳號:
- » 使用有人部落帳號:

有人出版社于2003年成立于馬來西亞吉隆坡﹐由一班年輕的中文寫作者組成﹐目前以業余方式刻苦經營。其成員背景多元﹐來自廣告﹑資訊工藝﹑新聞媒體﹑出版﹑音樂﹑電影甚至投資界。有人虛實並行﹐除了經營網上"有人部落"﹐也專注藝文書籍的出版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