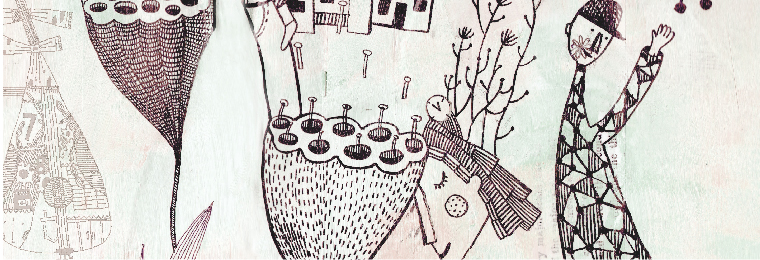梳声音︱ 被声音埋没之前
|
首頁︱鏡像︱購買出版品 |
|
6。破绽之城。重遇目击者甲
离开了温习过一千遍以上的后巷,天空突然亮了起来。虽然刚刚在后巷里行走的时候,还是黄昏,按照一般的常理,现在应该已经是黑夜。我到了一条崭新的街道上。街上极静。简直如Michael Sowa的画。咋看之下,这是一条可以处在任何城市的平凡街道。可是,若用心细看,这城市似乎处处匿藏着荒谬的事物。不,甚至,这些荒谬的事物,并不一定匿藏在什么地方。他们甚至大方地在最显要的地方曝露着。等待自己突兀的存在被发现,被撕开。可是这个城市的人偏偏见惯了,便一致认为各种不可思议的突兀的东西,都是理所当然、必然存在,无须置疑的。如果它存在,便必定是因为,它有存在的原因。
这时如果街角缓缓地蠕动着一只巨大的蜗牛,大概也没有人会细心地留意。像索瓦的画一样。安静。清冷。孤寂。平凡中藏着巨大的荒谬性。若不小心,就会被一切理所当然的现实的真实性所盖过。目击者甲在这时挥手叫住了我。我走进去他身处在的咖啡馆。
“今天没有下雨。”他说。
“你那天起就一直坐在这里?”
“一直在这城市里等待着。”
“等待什么?”
“如果能够捉住那隐隐藏在极平凡的街景中突兀的什么,我的人生或许因此而开往另一个我想也没想过的方向。我必须看见破绽。必须在平凡的街景中看出一个破绽。如果能从这极平凡的一切中看出那破绽,就可以从这里掀起那其实比荒谬更荒谬的真实。像从墙纸的破洞处开始掀开,就会发现墙纸下还有花色完全不同的墙纸。如果我那么做。现实就将被推翻了。”
“可是为什么要推翻现实?”
他慢慢地吐了一口烟。忽然因为想笑而被烟呛到。
“我也没有想过。。。很可笑是不是?”
于是,他搅拌着乌黑色的咖啡。玻璃窗外开始下雨。街心里的各色雨伞群突然晃动着。走向窗的另外一边。如颜色各异的水母或鱼群。 如好久以前舞池里不断旋转的女人和蓬松裙摆。我想起波尔卡。香槟。玫瑰。旋转。三拍。Pizzicato。史特劳斯。他这样盯着移动的水母群或女人腾空的裙摆移动着,却在搅拌咖啡的同时不自觉地逐渐睡去。
我看着玻璃窗外,那些明确地、不合现实的细节渐渐变得理所当然。街角这时有一只巨大的蜗牛缓缓蠕动着。我望向目击者甲。
他在梦中。我知道,他已经在这里太久。也许,便回不去了。
离开了目击者甲,这是我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所以一切看起来十分新鲜。对我而言这个世界到处都是破绽。目击者甲说,只要看见三个破绽,并向破绽局举报,便能回去原本我们所处于的世界。我想了想,觉得这真是容易极。离开了咖啡馆和目击者甲没多久便看见眼前一个女人撑着半粒柠檬的伞具经过。我心里便数。一。人行道上几根矮矮的柱子换成了小喇吧的三个键,二。再走下去,别人家的遮雨棚上的条纹原来是黑白的钢琴键。三。我突然觉得这个世界充满‘破绽’。
四。五。六。七。
可以安心走下去了。因为我知道,我一定能够随时回去。不。我还想多呆一会儿。在这里,到处皆是破绽的城市。
7. 继续游走
沿着这条平坦的街走下去。C大调。街道的名字。C大调上像我所住过的城市一样。笔直地延伸下去,直到看不见的地方。两旁的房子漆上了让人开心的亮色。仿佛每一处都有阳光照耀着。即使有些房子没有阳光照耀着,也可以触摸到墙上留着的,阳光的温度。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一直这样走下去。这条街很宽大,宽大得让我觉得自己太瘦小。
店里散发出各种味道。新式糕饼点的面包香气。不久后,旧书店。在过去几间就是杂货铺。有很多不同的味道,走廊上还晒着干菜和一些干物。摊在地上晒着。再后一些就是中医馆的药草味道。
我一直沿着C大调走去。这一条大道上很多人越过了我。在我背后消失了。我在他们之间行走。仿佛也在自己之间穿梭。他们的脸,看起来,像我的脸。又或者说,他们的脸模糊得很,以至我没有办法用更多的文字形容他们的样子。他们看起来和我以前住过的城市里的人,一样。但是却又似乎有些什么,是不一样的。他们像是‘原型’一般的人。像那些未经细雕的原型。已经被谁削出了一个大概的形状。却任由他们以那样粗拙的样貌生存着。
这些原型的人,不断地与我擦肩而过。而我,每次从他们身边的空隙走过一次,便缩小了一点点。那是一个不易察觉的一点点。可是我还是察觉到了这样的流失。
我想我已经比刚来到的时候矮小了三公分,虽然并不能确知,那究竟只是自己的想象,还是,如我精准的直觉般—真的矮了三公分。这样一直沿着大路走下去,恐怕只会慢慢地消失了吧。后来我在一个邮箱旁看见一条小小曲曲的巷子。上面有一个蓝色的路牌,标示着:
A 小调。
也许我该走进去吧。纵然里面看起来阴暗些。可是里面的路曲曲折折,看起来挺让人安心。刚走进去不久,就看见一座‘阳台酒吧’。 对,是一座。好几面墙。好多好多小阳台。这里就是阳台酒吧了。我旁边的一位侍者说。
8。阳台酒吧
那是好几面嵌了阳台的墙。墙上有许多不可思议的攀藤、钟(时间却没有一个是准确的,至少没有一个跟我的一向精确的手表一样)。每一个阳台上都有一盏灯,一张小桌子和两张椅子, 也有一些阳台上放置的是一张以前教堂用的木长椅。无论阳台上置有一张椅子,或者两张,一张长椅还是两张,这酒吧只欢迎独处的人,不容许更多的人在同一个阳台上。
我让侍者带领我去一个属于我的阳台。侍者带我攀爬了好久的旋转楼梯。终于到了墙的最高处。我们的头顶有一只巨大的古钟。
我指了指头上这顶大钟。问侍者:这钟,几点敲啊?
侍者跟我说,任何时间都有可能。
为什么任何时间都有可能?
你没有看见我们这里的墙上都是钟吗?
对啊,而且时间完全不一样。
对啊。所以时间在这里,一点都不重要。
我在‘我的阳台’上坐了下来。点了一杯饮料。侍者放下了饮料,便离开了。我安静地从这阳台看着这A小调小巷。咖啡的味道充斥着这条小巷。天色慢慢暗了下来,阳台上的小灯就逐个亮了起来。人们各自在做着自己的事,有些人在低头书写,有些在喃喃自语。有些则戴着耳机听音乐。有些盯着手提电脑飞速打字。阳台外的世界,都暗得很,像故意被调低色调的背景。
就如男孩那时在窗前看着窗外的屋檐一般吧,我想。
我熄了灯。灯熄了后,暗得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声音反而变得清晰。我听见了一些重复的声音。这些声音一直伴随着我。虽然我没有办法听见每一个音。但是,听起来就像钢琴演奏着重复的琶音。似乎从很遥远地地方传来的练习声。又似乎很近。我在长椅上躺着望着近深紫色的天空。这时,人们似乎都睡去了吗?
我不想睡。因为我不想入梦。梦总是过于破碎。让我无法拼凑出一个有意义的故事来。我知道只要合上双眼便能回到最初的那一条地平线上。无论今天走过多少个小巷子。别人家的草坪。校园。或快餐店。只要合上双眼便能回到那一天。
(目击者甲目击着一切的那一天。那时车窗还没有被沾湿。星座于是尚未成型。百褶裙还没有被车门吃掉。雨伞还来不及被撑开。)
我听着虫鸣声。因为你没有再翻阅,所以我睡去了。
9。抽屉的远行
醒来的时侯,我已经不是躺在阳台的木椅上。而是在一只抽屉里面。我坐了起来。望向外面。抽屉正在飞行。成群的抽屉从城市里逃离了。天空都是黑压压的阴影。二十八。二十九。我心里数着。开始不相信目击者甲至今未能举报三个破绽的原因。难道他看不到这里到处都是破绽?我想起目击者的话。
我该不该将这层壁纸撕开。
如果我那么做,另外一个世界便会显现。
我身处于的抽屉,开始远离了城市。并同时带走了城市里无数的抽屉。药材店那种刻有各种药物名字的抽屉。庙里那些塞满各种签诗的纸条的抽屉。老旧办公室里井井有条的铁皮抽屉。装满滚动着的彩色铅笔的抽屉。。。像末日一样遮盖了城市天空的一角。夜深了。抽屉的主人们也许正在酣睡。也许不会知道自己的抽屉在夜间集体逃离这回事。也许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而没有去破绽局举报。
如果一座城市在黎明时分突然没有了抽屉会怎么样。
我想象着别人抽屉里那些未完成,或完成却终未寄出的旧信。停止走动多年的手表。款式很旧的红包。照片。没有墨的钢笔。弹珠。不知多久没有翻开过的盒子。盒子里的电影票根。口红。走音的圣诞贺卡。纪念册。干花。等等。如果抽屉都不再回去,那么明天破绽之城应该到处都是别人抛弃出来的,剩下骨干枝条的柜子吧。
为此我突然感到非常哀伤。虽然破绽之城理应不是我所该处于的城市。但是,却有些什么,似乎与我紧紧相连着。
抽屉移动的速度非常缓慢。仿佛恒久在移动。又仿佛恒久静止着。在时间或者空间里凝结了一般。
我翻起了我处在的抽屉里的一些纸张。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一些字。
拔萝卜。拔萝卜。
嘿哟嘿哟拔不动。
老太婆。快快来。
快来帮我们拔萝卜。
这些字写在一个发黄的信封的后面。我不知道是什么人拥有这只抽屉。抽屉外面还粘了一些脱色的卡通贴纸。我开始唱起这首歌。风很大。我把这首歌重复唱了好多遍以后,终于看见一些抽屉已经开始在一个很空旷的地方降落。
我的抽屉着陆了以后,我便从抽屉里走了出来。空旷中有数以万计的抽屉,和变成抽屉以后的阳台。我看见一只很熟悉的抽屉。它躺着,曝露于空旷中,潮湿。它的胸口长着一棵树。树上长满果实。叶子绿得很。树下堆满了很多纸张,都是信。或是写不完的小说。那些字迹,都是我日日看见的熟悉字体。
我走了过去。望了望四周。旷野中躺满了抽屉。有些长出一朵白色小花。有些是一个迷你湖。有些是间房子。有些是囚牢。有些载着长颈鹿。
“你看见三文鱼粉红色的游云的那个夜晚,其实已经看见我了。” 抽屉说。
“但,那不是我。那是我小说里曾经存在过的男孩。”
(男孩最终说话了吗?我忘记了自己在小说里的安排。也许就永远因为我未能完成这小说而永远沉默着在他的世界里不断地走着,在别人的后面,走成一条长长的距离--然后不回来了吗?)。
“那便是你。”
“那么这里是哪里?”
“这里是所有抽屉在晚间休息的地方。因为我们盛载着别人的故事,很累。不时会集体离开。带着别人的故事来到这里,空旷的地方,平躺下来。也需要休息啊。” 抽屉说。
“那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
“因为你是故事。也是抽屉。”
10。雨不曾停歇
天色渐亮的时侯我醒来了。窗外下起雨。我把窗口打开,呼吸那含土香的空气。窗外如雾,我读着抽屉给我写的信。她从远方寄来了这一叠新故事。并没有提及她现在哪里,或者,以她的语气来说--我不知道她现在在哪一个远方。信的最后一页这样写着:
来到你三十岁的转折了。我想为你写一部小说。一部,当然说得过于庞大了,我没有那样的能力,你也知道的。好吧,我为你讲一个故事。这故事一直破碎地存于你的抽屉多年。哪个抽屉,也许你已经不记得了。
“不是吗?我们从未完整过。”
有一天你那么说着。好像是说给自己听的。而我却听见了。是啊。我们从未完整过。连为你说的故事,也因为尝试着完整而破碎了--这些,你的。破碎的话语。情景。一直为我撑着一个。另外一个。世界。平行进行着的。充满破绽的世界。
我读着读着终于读到信末。她用了新的一张纸,这么写着:
你不是常常问我吗?
我常常说要为你写一封长长的信。你问我说。多长?六十公里?还是地球圆周那么长?还是十万光年?
很抱歉。都没有。
但这是我能给你写的,最长的信了。
(完)
[ 點閱次數:5655 ]
請用以下一項機制登入或註冊:
- » 使用Facebook帳號:
- » 使用有人部落帳號:

有人出版社于2003年成立于馬來西亞吉隆坡﹐由一班年輕的中文寫作者組成﹐目前以業余方式刻苦經營。其成員背景多元﹐來自廣告﹑資訊工藝﹑新聞媒體﹑出版﹑音樂﹑電影甚至投資界。有人虛實並行﹐除了經營網上"有人部落"﹐也專注藝文書籍的出版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