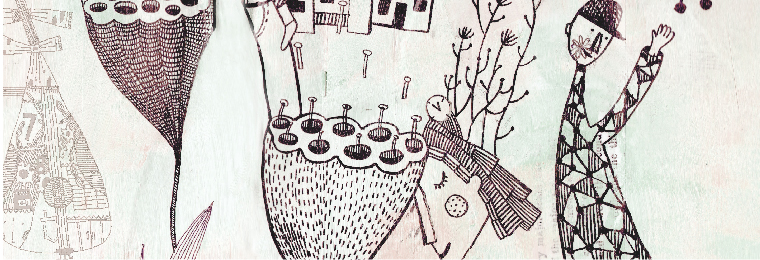梳声音︱ 被声音埋没之前
|
首頁︱鏡像︱購買出版品 |
|
頁數 : << 1 ...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

我和红毛丹树都曾经是蚂蚁的朋友。树干上一定爬着一列列的黑色蚂蚁。阳光在地上都是碎片。我的时间,很多。很长。用不完。
胶园里的公共诊所前面,是我玩蚂蚁的地方。空气中有我熟悉的味道。各种药混在一起的味道。阳光?阳光很斜。很辣。我的手正为蚂蚁建窝。双手堆起泥沙。想象给蚂蚁建一个大别墅。你们有多少个。当时我问。内心数着。怎样建一个有很多房间的大别墅。我可以让你们每一个都有自己的房间哦,我喃喃自语。
结果把一堆沙堆在红蚂蚁身上。一下子把蚂蚁都盖了起来。没有了。
姐姐走了过来,说,你这样不是在为蚂蚁盖房子。你要活埋他们啊。
我一惊。怎么办。我把一百二十三只蚂蚁活埋了。我别过头去。不敢相信自己杀了这么多蚂蚁。直到后来几乎忘了这件事的时候,回过身来。蚂蚁还不是一样在那里,列队走出来。才没有那么容易死呢。
蚂蚁心里也许忍不住这么说。笨蛋。
[ 點閱次數:6257 ]
我们都叫她梳小姐。因为她的工作是梳声音。我住的这个城市叫破绽之城。至于为什么叫破绽之城,我也不太清楚。老一辈的人,也许比较清楚。譬如我父母,他们就会说,听说你公公婆婆来到这城市的时候,看见到处都是破绽,所以他们就称这里为破绽之城。可是,我长得那么大,有多大呢?三十岁了。却从来没有看过破绽。也不知道破绽是什么。只是知道大略是,一种与现实不符,或漏洞之类的东西。说实在,我想我懂的也很少。即使我父母吧,每次我问他们,破绽之城为什么叫破绽之城,他们也说不清楚。总是赖祖先。
祖先这样说就是这样说。不要问那么多。
[ 點閱次數:5370 ]

photo/clumsybee
第一次和壁虎小姐相遇,是在一间专门提供精致的起士蛋糕和意大利面的小咖啡馆。我一个人,壁虎小姐也是一个人。冷气十分冷,外头的太阳却看起来十分烫。我们的桌子上都有一杯非常冷的白开水。那种一看就知道喝下去也许会闹胃痛的白开水。
她叫了一份小起士蛋糕,上层是红色的果酱。后来听店主说,那是大红花和一些红色的果子合成的一种特别口味的果酱,带酸。酸中带甜。店主解释着他们店里的每一样口味的起士蛋糕,我的眼角看见了他身上的花色衣服,那种在视觉上让人无法越过他而忽视他的存在的华丽花衣。或者说,看着他的衣服花朵的摆动,会不自觉地忘了留意他说话的细节。我于是低头叉着我那盘沙拉,叉起一颗沾有陈年红酒醋的小番茄,偷偷听着他解释着每件蛋糕的制作过程,和面对的挑战,解决的方法以及他坚持做得和别人不一样的理由。虽然,我对蛋糕,一窍不通。
壁虎小姐似乎很认真地听着。她的蛋糕非常小巧,简直可以说,如果要的话,一口就可以解决掉的蛋糕。小巧的蛋糕摆放在一个白色长形的瓷盘子正中央,旁边摆了两颗切成半的草莓上面还有非常细的白砂糖,让人倍感温馨。草莓红,叶子绿。奶油黄,雪白和巧克力沾酱。一副节日感强的样子。
我注视着他们。他们的身影像正融合在一起的多边形。也许是我近视又没有戴眼镜,所以总觉得他们和那样的背景是完全融合,没有菱角的。反倒是我自己,像一个完全不能融入的外来者。我看着我脚上的拖鞋和牛仔裤尾的白色丝状线条,像婚宴中大家吃剩的鱼肉般凌乱,更不用说我的头发,长而凌乱地盘起,像理发院里散落着的黑色头发一样密集又疏离。
[ 點閱次數:6047 ]

说实在的,有时还觉得自己身处于车内,身处于颠簸的路途中。有时会以为自己还处于那不断看外面的云的日子。即使那样的日子并不长。奢侈得很。我大概不时会想起这些你没有参与过的片断了。
屋外的电梯升级工程开始了。准时地发出马达的声响。为半睡眠中的我上了链,于是我行走起来。
每天,无可避免地行走于这些短暂的新路。每一天都有很大的不同。有时我们被引至弯弯曲曲的人行道。高低不一的路,被人用木板衔接起来。踏上去发出下面空洞的夸张声响。我们两旁竖立了颜色鲜艳的锌板把我们引至可行的新通道。我们在窄小的、暂时的通道,相互礼让着。笑着,有时相视。有时不。有时专注地走着。也许各自想着各自的事。穿着荧光黄色十字的工人手上提着十多盒保利龙饭盒低头走来。
说不出对于这样的改变,于我有什么感觉。原本很宽的路,更宽了。
不是吗。我们都没有发现。每天究竟有什么被移走了。有一天突然发现那条叫‘过’的马路又宽了,更难过了。路旁更光了。每天这么走着,却说不出来,究竟哪里不同了。像是有人还跟你玩那一个报纸上常常有的,你小时喜欢的,游戏。
似乎有人在背后对你说,嘿。怎样。找到了没有。
(注:我每天必须过的马路,叫'Cross Street'。可以自己解释为,过。或者,十字路口。无论马路叫什么名字,都是必须经过的一条大马路。同事也常常不记得这条路的名字。要过去马路另外一边吃午餐的时候,有时必须说起,就是那条马路啊。那一条?过马路。哪一条是过马路? 难过那条。)
[ 點閱次數:5899 ]
羽球场湿了。灯打着,运动场跑道那种红。乒乓桌那种青。马路虚线那种白。白色灯光照在其上,黑暗中的羽球场,好像假的。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发现这里有两个羽球场呢?因为今天下雨。因为我没有带伞。
正要走到地铁站的出口,雨突然下了起来。刚才明明还很小。突然变大。sf的雨声罩住所有人。有雨伞和没有雨伞的人。我几乎要走到出口甲,结果必须倒退,往另外一个出口走去。出口乙。我已经很久没有从出口乙出去了。因为搬过一次家。一直嫌这边必须过人行天桥。要走楼梯。但是今天不得不走这里了,因为这里有盖。一路有有盖走廊,不怕淋湿。
就是刚从人行天桥下来不久的一段路时,看见篮球场突然变成了两座羽球场。正湿湿地反光。
[ 點閱次數:5929 ]
韵琪是我小学、中学最重要的朋友。可以这么说,我小学并没有朋友,只是一直跟在她后面,像是她的附件般认识她认识的朋友、读她读的书、念她念的学校、喜欢她喜欢的食物、参加她参加的活动。
初中一的时候,她每天上图书馆。图书馆这种地方是我其他朋友不太想去的地方。太高。太远。太静。但是我的朋友韵琪却每天上去借书、还书。我没有更重要的事做,所以那段时间多半也会跟她上图书馆。翻看书柜里的书,尤其喜欢翻看最后一页看借书卡上的名字和日期。那时很多书都有她的名字和字迹。字体饱满,方正,通常是钢笔书写出来的,有一种吸引我的润泽(后来我也学她买了钢笔)。在她的名字下面,常常便是我的名字。当时我就是这样的人。不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凡是都一副无不可的模样,跟着她做她做的事。
我有几个习惯,都与她有关。譬如,我喜欢在买书之前嗅书,喜欢用手指触摸书的页面凹凸。譬如,我习惯用墨水笔,不太用原子笔。
初一下半年,学校铜乐队招收新队员。她举手。我也举手。那一年的新会员只有五人。记得第一次拿乐器的时候,队长看了看我们的手指,说,非你们莫属。然后神秘兮兮地转身进入乐器室端出两个盒子递给我们。
“你们的。”
[ 點閱次數:7410 ]
碧芝不是人。她是壁纸。可是她老是以为自己是人。好吧,碧芝如果是人的话,也是一个让人觉得没有存在感的人。像我们走进一间屋子,最先看到的就是那屋子的主人,或沙发之类的。壁纸也许提供了某一种气氛,但是大部分的时候都只是是一种似乎存在着的东西,不太会被认真注视着。至少大部分的人不会留意。碧芝自己当然不这么认为。
碧芝身为壁纸这件事,说起来,只有我知道。碧芝这张壁纸身上有着菱形的纹。似有若无地浅浅印着一排排的图纹,延伸到天花板的边缘去。碧芝总站在墙边听着别人说话,以一种具有距离感的方式参与着人们。不,她会说‘我们’。因为她以为她也在一个距离外注视着自己和别人,虽然在别人的圈子里头并没有包含碧芝这个‘人’的存在。无论到了那里,她总是与墙壁同色,或者,总是化成一些简单的重复性图案,成为了气氛的一部分。
碧芝脸上唯一的装饰品是钟。人们其实在谈天中开始注视到她也是因为她眼睛上的那颗钟。
啊。六点了。要走了。人们看了看‘她’后说。然而我们都知道,人们看的不是碧芝而是钟。人们不会在她身上花时间。
那么我是怎样发现碧芝的呢?
[ 點閱次數:6223 ]
手臂小姐是我认识的朋友中,外形最为突出的一个。她长得。。。老实说,普通得很。甚至可以说,不起眼。眼睛不大,糟糕的是,也不是那种很东方的小眼睛。总之,介于两者之间,眼睛似双不单,似单不双。很抱歉地说,就是平庸得很。
手臂小姐之所以被称为手臂小姐,当然是有缘故的。她是我中学时的同班同学。记得中学时有一节课叫自修节。原本校方当然希望我们用来作自修用途,所以没有老师来上课。可是,我们班上真正自修的同学,不多。倒是因此有了不少即兴讲课的项目。有些同学会站出来自以为是生物老师般地讲解生物课。有些同学会拿一个吉他出来唱唱歌,有时班长会站出来要我们表决是否要共同写信抗议某老师教学不良。总之,是一个很难以预测的四十分钟。看不下去的同学往往将头伏在桌子上大睡一觉。
有一天,不知道什么原因突然有人提议要为全班的女生作一个大评分。有人拿了老师用的点名单,发起了‘评分大赛’。其实,手臂小姐便是这样产生的。某男生按照名单顺序念出女生的名字。
陈静仪
陈淑芬
陈美愉
方若宜
姜小曼
。。。
。。。
[ 點閱次數:5052 ]
請用以下一項機制登入或註冊:
- » 使用Facebook帳號:
- » 使用有人部落帳號:

有人出版社于2003年成立于馬來西亞吉隆坡﹐由一班年輕的中文寫作者組成﹐目前以業余方式刻苦經營。其成員背景多元﹐來自廣告﹑資訊工藝﹑新聞媒體﹑出版﹑音樂﹑電影甚至投資界。有人虛實並行﹐除了經營網上"有人部落"﹐也專注藝文書籍的出版和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