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不入︱ 我是激流島上一棵樹。
|
首頁︱鏡像︱購買出版品 |
|
Posted by Sinigel Ng in 思奈焦部落
on 5.30.2009

那些不喜歡讀詩的人,正在天堂裡睡覺。
——毛毛之書.1
深夜讀《毛毛之書》,書太薄,輕盈得好似手中拿著的是一張寫了詩的紙,而並非一本詩集,它的重量似乎比一杯茶還輕,然而詩人的思想是靈傑的,會騰空而起的,不受重量束縛。
詩集的封面幀裝,滿是螢粉紅,夜裡在光的照耀下,真的會閃爍著螢光那般;內頁排版宛如華文小學一二年級時的課本,中文字底下安放了羅馬拼音。對於經歷過中文課本有羅馬拼音附注的小學時代的人,到底是要感到親切的。2007年有人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我是遲至2009年的今日,方才將其讀完。
一般時候我不讀詩。不讀詩的理由可以有很多,好比我不寫時、寫不出詩、感覺不了詩、冶煉不出詩的文字……有了這些原因,我不寫詩,再來也不渴望成為詩人,甚至放棄寫詩。因為一本或一首詩的回籌率實在太低,甚至比一篇只有三四百字,通篇我我我的「肚臍眼」小文還不如,利益當前,詩養不起一個人,所以我不寫詩。
但是,讀詩有時是一種消遣。好比你讀陶潛、你讀徐志摩、你讀喬叟、你讀歌德的浮士德、你讀聖經、你讀佛經里的偈。因為有這些詩在,所以有了神話。周作人在《雨天的書》裡面曾說過,神話創作者並沒有隨著時代的變遷消失,只是他們轉而變成了詩人,繼續創造神話,創造神。
現在想起周作人的話,不禁要將之和木焱的《毛毛之書》嵌合在一起。當然,這本書沒有多少的深刻,卻有一定程度教人省思的地方。尤其是詩人所寫的戰爭詩。詩人在戰爭詩中,每個字所營造出來的同情與憐憫,「自腐爛的戰地」與讀者同在。
不過,我還是覺得詩人是浪漫的時候多。好比詩集中,不時會閃現出來的,寫詩與散文,散文與小說與詩之間的血緣關係。也許,詩人是想成為一個屬於「妳」的散文家,想在寫小說的時候,成為一個「他」。那麼,寫詩的時候,詩人是否想成為「女」字部的他、你,抑或詩人根本就是處在「中性」的位置,來詮釋世界,解釋詩人所見的實況,人生不可思議的苦和樂?
「以前的天空是甚麼顏色的」?類似的童稚的語言的詩句,在《毛毛之書》中隨意翻閱,拈一句便是。我佩服的是,詩人這般年紀猶能以童稚的目光,描繪出成年人自孩童蛻變之後的「屬性」。那些來自成長的變化,慾望的、利益的,夢裡的、情人之間的……將那些關鍵字鏈結,我想便是詩人的合成體。
若你問《毛毛之書》適合誰讀?這本書在哪裡閱讀最為適合?在我看來,深夜讀較好,入眠之前,來個輕盈簡短的感性。哪裡讀?可以的話,站在書局或圖書館讀是不錯的。在那樣人來人往的環境下,詩人的思想在詩句中轉變,你亦隨著詩人的轉變而轉變,唯有站著才能體會到「宴會里/笑聲/親吻的酒杯/水晶燈下/被侍者認出來的//ABCDEFGH我JKLMNOPQRSTUVWXYZ」的感情、時間和影子。
[ 點閱次數:13370 ]
──悼德語詩人保羅.策蘭(1920-1970)
“有時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心的苦井中。"
被咖啡黒攪動,在命運中加入牛奶攪動
有時候加糖,有時候不加
貫穿食道的寂寥,酸腐的胃囊
身體內冷冰的遺跡
繼續哀悼紅花,更多哭瘦的黃葉
風吹動沙塵旋繞在
這個荒廢的噴水池
中央的雕像斷了手臂
與遠去的藍天相映,陰雲緊盯逐放的水湄
一顆擲向不安的石子
定定地墬向苦難的深部
追隨死神歡笑的聲音
“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啟示之星奇異地閃現。”
註1:1970年4月20日,策蘭在塞納河投水自殺。最後留在他書桌上的是一本打開的荷爾德林傳記。策蘭在其中一段劃了線,“有時這天才走向黑暗,沉入他心的苦井中。"而這一句餘下的部份並未劃線,“但最主要的是,他的啟示之星奇異地閃現。”〈死亡賦格〉是詩人第一首公開發表的成名詩作。
陳燕棣評語:第一次讀這首詩,我覺得其實寫得最好的部分,是開頭與結尾的引用詩句。第二次讀,發現作者將點題和破題出讓給引用詩句,原創的部分其實有內隱張力,層層疊疊的黑色哀愁貫穿全詩。詩的語言成熟細膩,意象飽和,是不錯的作品。
方路評語:一首成熟的詩,藉此向苦難的大師致敬。寫出沉鬱的力量。
張永修評語:作者以詩人策蘭臨終前閱讀的傳記文句為詩的引子和尾聲,暗示了詩人的人生際遇。作者用攪動“咖啡黑”,加牛奶,加糖或不加,顯示了詩人寂寥與窮困(酸腐)的生活。第二節的荒廢景像是為死亡鋪陳的場景。第三節是詩人選擇死亡方式的想像。詩人是“一顆擲向不安的石子”,雖然“陰雲緊盯”,他卻是追隨“歡笑的聲音”而去的。這一節的意象處理得很好。是很好的一首悼亡詩。
延伸閱讀:第一屆游川短詩獎優選作品<�吶喊>
[ 點閱次數:16045 ]
1. 什麼是詩(infinite)?(什麼是哲學)
這個問題或許只能很晚才提出,等到步入遲暮之年,能夠具體而微地談話的時候。有關這個題目的文獻實際上並不多。這是一個適合內心思緒紛湧的午夜,在沒有詩可寫的時候才會提出來的問題。這個問題以前提出過,而且一直在提出,不過方式過於間接或拐彎抹角,過於造作,過於抽象,而且提到時總是居高臨下地一語帶過,並沒有被它緊緊扣住。那時候我不夠清醒,創作詩歌的欲望太強烈,所以除了拿這個問題當文本習作,根本沒想過詩到底是什麼,沒有做到最終放棄咬文嚼字而直截了當地捫心自問:我寫了那麼久這個東西,可它究竟是個什麼?
撰改自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1991). Trans. What Is Philosophy? (1996).什么是哲学?德勒茲與瓜塔里(Félix Guattari)合写
2. 真摯性與技巧性(infinite vs. finite)
林亨泰:假如寫詩是技巧的運作,而非真誠的人生感受,寫詩可能缺乏真摯性。同樣是隱喻的運作,成功與否,就在於詩人對於人生感受的真誠。
當寫詩是屬於有限(finite)的文字創作,如何在有限中寫入無限(infinite)的美的價值,取決於詩人對待生命的態度。如何運作無限?變成一個詩學上的重要客題。真誠是美學價值之一,美學價值並不是簡單的被定義為「美」和「醜」,而是去認識客體的類型和本質)。
問題:創作是我手寫我口(真誠嗎)或我思故我在(無限的意識流也有真誠)或創作是真實的虛構(謊言的技藝)。對於創作的定義與探討,這些說詞都成立,關鍵在於不同時代背後之社會價值下,所呈現的面貌與表述方式之有別而已。偉大的命題始終在那裡,不變。
我聽見有個足音──我的眼前無人無影/驟然回頭一看,除了自己空無一人/在這險峻而寂靜的山徑上(詹冰〈足音〉)
哦親愛的主願祢明白/我所信望的憂愁與愛/此刻都早已長成一場/晚來的大雨蔓燒/在深如方格的夜(木霝〈一名無業詩人的睡前禱告〉)
布丁還在桌上/不敢卸妝/九點了//它嬌嗔地要我/給個交待//我趴在它的耳邊/輕聲細語/等我……(劉小梅〈布丁還在桌上〉)
「一整天我在我的小屋裡流浪,用髮行走」(商禽〈事件〉)
除了燈火翻譯的山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除了勞倫斯詠嘆的蛇之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想必是觀音……蛇游進他看不見的詩裡了(陳義芝〈海邊的信〉)
美學審美柏拉圖、亞里斯多德文藝復興理性主義經驗主義德國唯心論浪漫主義(為藝術而藝術)現實主義(社會責任)現代主義後現代(解構)
現代主義:意象主義玄學派象徵主義立體主義未來主義表現主義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前衛主義
審美的基礎條件:
不同審美觀帶來不同的表現方式,不同主義卻是想掌握大眾的審美而歸納出來。
以現實為思維對象的詩不能只是現實的複製品,更不是反映現實的工具。
3. 詩歌語言:古代與現代(古代≠古典)
詩是一種語言的純粹,不代表任一象徵。
北島:現代漢語確實存在西化的問題──它的語言結構、表達方式、音樂性;其實在文革時期,早期的6,70年代,為了脫離官方話語的控制,西化過程是一個必然過程(木焱:台灣現代詩的西化是紀弦創立《創世紀》詩刊,引進現代主義)。我曾經嘗試過把古代詩詞與詩歌語言、意象融入到現代詩歌(例如〈青燈〉),和古代詩歌的神韻結合、語言結構、音樂性、節奏,所以現代漢語詩還有很大的可能性。詩人想改變語言的方向,卻又受限於語言,他的創作工具是語言,所以更難跨越了。(蕉風500訪談內容)(木焱:我們的詩歌/文學環境還不夠廣泛、眾聲喧嘩,在先天營養不良下,現代漢詩要如和向前邁進?)
Martin Heidegger:語言是一種存有。
梅洛龐帝:語言一直在喚醒我們,使我們以口、肢體、意識相互交融而發出言語,是「語言擁有我們,而非我們擁有語言」。
木焱:詩找上了我,而非我創造了詩。
Jonathan Holden:綜觀美國後現代詩人的詩作,可以發現大量的非文學的近似體被援引為詩的語言,其中以會話(conversation)式的語言最具特色,其語言實與散文無異。例如:金斯伯格〈嚎叫〉木焱〈年代〉和〈2〉于堅〈零檔案〉許赫〈邊境牧羊人的晚點名〉〈診所早晨的寫生作品〉
現代漢詩西化後產生的口語詩、白話詩這一種類,自五四發展至今才短短90年。相對於西方悠久的詩歌史,現代詩只是學習期,尚未發展出現代漢詩的獨特。
可參考《當代台灣新詩理論》孟樊著。
我調整時差/於是我穿過我的一生//蜜蜂成群結隊/追逐著流浪者飄移的花園///清醒的石頭在我腳下/被我遺忘(北島〈在路上〉)
故國殘月/沉入深潭中/重如那些石頭/你把詞語壘進歷史/讓何道轉彎
花開幾度/催動朝代盛衰/烏鴉即鼓聲/帝王們如蠶吐絲/為你織成長卷
美女如雲/護送內心航程/青燈掀開夢的一角/你順手挽住火焰/化作漫天大雪
把酒臨風/你和中國一起老去/長廊貫穿春秋/大門口的陌生人/正砸響門環(北島〈青燈──獻給歷史學家Fred Wakeman〉)
2001年10月23日,我誕生在台北市文山區
萬盛街153號4樓的單人床上
木焱歸還我名字:林志遠(簡寫是林志远)
馬來文叫LIM CHEE WAN,居留證上的名字
從現在開始,我又是林志遠了,並且已經畢業
多棒!我不會寫詩,這些頂多是一則故事,有關我和
一個叫木焱的關係,有點兒曖昧,因為他在躲藏
他在我體內,不知道是死是活(木焱〈年代〉)
木焱〈噢!〉小我的抒情
金斯伯格〈嚎叫〉前段,大我之顯見乃眾多小我之累積。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
天使般圣洁的西卜斯特渴望与黑夜机械中那星光闪烁的发电机沟通古朴的美妙关系,
他们贫穷衣衫破旧双眼深陷昏昏然在冷水公寓那超越自然的黑暗中吸着烟飘浮过城市上空冥思爵士乐章彻夜不眠,
他们在高架铁轨下对上苍袒露真情,发现默罕默德的天使们灯火通明的住宅屋顶上摇摇欲坠,
他们睁着闪亮的冷眼进出大学,在研究战争的学者群中幻遇阿肯色和布莱克启示的悲剧,
他们被逐出学校因为疯狂因为在骷髅般的窗玻璃上发表猥亵的颂诗,
他们套着短裤蜷缩在没有剃须的房间,焚烧纸币于废纸篓中隔墙倾听恐怖之声,
他们返回纽约带着成捆的大麻穿越拉雷多裸着耻毛被逮住,
他们在涂抹香粉的旅馆吞火要么去”乐园幽径“饮松油,或死,或夜复一夜地作贱自己的躯体,
用梦幻,用毒品,用清醒的恶梦,用酒精和阳具和数不清的睾丸,
颤抖的乌云筑起无与伦比的死巷而脑海中的闪电冲往加拿大和培特森,照亮这两极之间死寂的时光世界,
……
从他们自己身上剜出的这块人生诗歌的绝对心脏足以吃上一千年。
4. 另一種審美/講述的方式
John
Berger:照片是一個交匯之地,在那裡,拍照的人、被拍的人、看照片的人,以及使用這些照片的人,他們的種種興趣和利害關係常常是互相矛盾的。這些矛盾既掩蓋也強化了攝影圖像本身所具有的歧義。
大多數關於攝影的理論寫作都局限於單純的經驗描述或單純的美學思辨。然而,攝影自然會提出現象本身的意義問題。(木焱:創作者為了將其創作的對象地位提昇,往往神格化這些對象,好比語言、攝影、舞蹈、文學、詩歌。)
木焱:蒙娜麗莎的微笑被盜,人們卻欣賞畫作被盜之後留在牆上的畫框印。國王的新衣一樣寓言了俗民的觀看角度,往往受媒體、學術理論、強勢言詞所影響。詩人必須有自覺於外的靈性,超然的感受力,但這些往往只在年少懵懂時期才會發生,因為那時對事物的新鮮感,延意出種種詮釋,或許有錯誤,卻是美麗的錯誤。
美國文學批評家布魯姆(Harold Bloom,1930~
):若要走出前輩詩人的陰影,就得拋開歷時性的束縛,也就是超越歷史和時間進入純文本性比較。對於這種比較,後來詩人和前驅詩人的作品實際上都不是獨創的或獨立的”詩”,它們只是各種前人的”詩”的文本的交叉體現(intertextuality)。
木焱:寫詩是不及物動詞。
1. 延伸閱讀:臺北,木焱;影響的焦慮,Harold Bloom;中國先鋒詩歌論,陳超;台灣當代新詩理論,孟樊;Another Way of Telling,John Berger;文明的孩子,Joseph Brodsky;西方美學簡史,Monroe C.Beardsley;診所早晨的晴日寫生,許赫;時間之書,里爾克;藝術的精神性、藝術與藝術家論、點線面,康丁斯基著;美學理論,阿多諾著;深淵,瘂弦著;十三朵白菊花,周夢蝶著
2. 現代詩辭典
「詩的語言」
整理/謝三進
1.
何謂詩的語言,簡單的說至少要是比喻性的語言,也就是一種「代替」與「轉換」的功能。詩不可能直指真實,詩也不真實,但詩是真實與說謊的辯證,這種辯證隨時引伸新的可能,那可能即意義本身,詩的意義就在一物與一物之間的轉換,事件與事件之間的引伸,其不等於純然的客體描述,何來客體之真實展示呢?……所以尼采自一八七三年寫出「隱喻語言之荒謬」,古典修辭家視隱喻不過為修辭技巧,尼采提升它,以為吾人認識客體之基礎,並且是一切語言之表徵,特別是詩的語言。
──〈一首問題詩的問題詮釋〉
游喚1980
2.
美國1950、60年代的「紐約學派」(New York School)(超現實主義一派)著名詩人布萊(Robert Bly ,
1926-)以為:「詩表達出那些我們剛剛開始想到的、還沒有思考的念頭。」(The poem expresses what we are
just beginning to think, thoughts we have not yet
thought.)他說感覺是難以形容的,所以必須依賴意象──我們的「夢境語言」──來表達感覺;用意象試圖描述我們意識難以企及的真理。
──〈西方現代主義流派簡釋──超現實主義〉
陳義芝(收錄於《聲納──台灣現代主義詩學流變》2006 )
3.
詩語言會夸夸其談其實是修辭策略的運用。修辭是詩人巧妙地發揮想像情境的一種高級藝術,也是充份表達思想的一種手段。但古人也說過,文欲其工應在情欲「信」的前提之下,才可獲致「巧」的效果。……
在文學藝術中,英國詩人雪萊對詩的解釋是「詩乃想像的表現」,因為豐富的想像力可以使不具形的思想實感起來,可以使平面的東西立體起來,可以使死板的文字生活起來。而一般讀者的惰性是十分厭惡那種陳陳相因的構思,似曾相識的形象和人云亦云的語言。詩人乃運用想像力,不照既有和現成的規範,獨自地創造出新的形象,變為新的意象結構與藝術情境,以迎合讀者喜新厭舊好奇的心理。……詩雖出於想像,卻仍離不開客觀事實之對證,詩可以無中生有,但不可有卻無脈絡可尋。
──〈第62問 白髮三千丈?〉
向明(收錄於《新詩 後50問》1998)
4.
現代派(紀弦等)主張要把西方自波特萊爾以來的整個形式技巧,甚至觀念橫的移植過來,這也是後來(一九七零年代)遭到嚴重批判的癥結所在。詩所遭受的批評除了逃避現實之外,最明顯的指責是在詩的語言方面。……(然而)歷來文學家似乎自覺到文學表現所蘊涵的真理與科學論述所蘊涵的真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因此許多的文學家及理論家想盡各種辦法辯說詩的真理也相等於科學的真理。二十世紀的早期,英國的I.A.
Hicards曾指出詩的陳述只是一種「擬陳述」(pseudo-statement),也就是說,詩不見得要像科學論述那樣有精確的邏輯,詩所呈現的真理及詩所用的語言必然有別於普通的言說(discourse)形式。
──〈五四看臺灣文壇──一個理論架構的省察〉
蔡源煌1984
5.
詩的語言與散文的不同,以童謠式的歸納法來說,那就是:「一精二舞三重複,四美五韻六不盡。」
分開而言,詩的語言首先講求「精」,散文可以全盤托出,從頭到尾,詳細描述,詩卻只能擷取最好最精要的一段來表現,詩的語言必須是濃縮的,以有限的語言包容無限的情思……
其次,如果說散文像散步,詩就像跳舞了,散文是一步一步來,有一說一,循序漸進,詩卻是跳躍的、旋轉的,詩的語言「點到為止」,從這點馬上跳到另一點,中間略去許多線索,詩的語言不能像流水帳……它必須像舞步……在一定的規律中求取變化。
第三,詩不怕重複……重複的語言在詩裡是正格,可以達到迴環吟誦的效果。
(第四)詩語言的另一特色是求美,詩語言的美是經由人工錘鍊,以求接近自然的美,詩語言的美是創造的美……
第五項是韻,韻律的美最基本的表現是押韻,其次是長短句的變化,中國字一字一音,很能控制字的節奏……詩的音樂性較諸散文重要得多了。最後,詩貴含蓄,不要把話說盡,讓讀者也有體會、深思的機會。
──〈什麼是詩的語言?〉
蕭蕭(收錄於《青少年詩話》1989
[ 點閱次數:15998 ]
──談陳燕棣的詩作〈光〉(刊登於第18期字花)
作者按:陳燕棣,1975年生於馬來西亞。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現為媒體副刊編輯。曾獲馬來西亞第一屆中協全國大專生文學獎小說三獎、第十二屆全國大專文學獎文學評論佳作、第三屆全國詩歌創作獎佳作、第九屆花蹤文學獎馬華新詩首獎等。本文分析的詩作〈光〉,乃陳燕棣獲第九屆花蹤文學獎馬華新詩首獎的作品。詩作全文見本文附錄。
首先我們找不著這位創作者的著作,很可惜她還未出書。不過作為一個細心的嗜讀者,不難在網路上、報章上一覽她諸多文類且不同時期的創作,無論現代詩、散文、劇本、小說,皆有佳作。最近,這位創作者獲得一項文學大獎,毫無例外的被編入了馬華作家的行列,如果你還未曾讀過她的作品,不妨就從這首得獎詩作開始。
讀陳燕棣這首詩〈光〉,第一印象是「難讀」,然後「很冷」──像一部沒有高潮情節的電影,你又不捨得中途離席,因為評審們已經在開場前跟你說了,這部很有價值,而且是部「本土藝術電影」。
其實「難讀」的是詩作的斷句方式而非字句用詞,作者用了許多標點、括弧、凌亂的段數;時而把一個完整句攔腰切斷,時而來一段弦外註解。這種斷句法很可能對許多初學詩、寫詩的讀者造成閱讀上的障礙,導致沒有必要的誤讀與過度詮釋,可是卻不會對文學獎評審構成障礙(頂多是對中文語病的挑剔程度不一),反而可能因為作者的大膽斷句,與其他參賽作品的循規導矩相比之下來得突出,而獲得評審放慢腳步來欣賞與分析。
是的,閱讀這首詩時必須準備放慢自己的心情與閱讀的速度。讀詩原本就忌快,因為一般上詩短字少,一首50行的詩總字數也不過500字,每字每句都是詩人對待生命的焠鍊,不放慢速度閱讀怎麼能體會,連標點符號都是不能放過的路邊風景了。標點不是詩的點綴,它在這裡代表了詩人的面容,他在寫作詩歌時的表情與情緒,因為標點句讀幾乎決定了詩篇的語氣與唸朗的節奏。我們「讀」一首詩(而不是「看」一首詩)時,如果沒有正確的念法,很容易理解/體會錯誤,更有可能被自己的思緒打斷而讀不完一首寥寥數行的詩篇,而與詩中靈光擦身而過。
一、那是一道怎樣的光?
「光」無疑是這首詩的主角,電影能呈現出影像得靠光線的照射,我們才能在白色布幕上看到創作者說的故事;而作者尋找「光」,在每一個場景裡發現「光」,就是他這部影片的主題。
來自哪裡的光,去往哪裡的光,回憶裡的光,流失的光,進而定義了自己的光,分析了古人的光,革命者理想者的光。光表示能量,作者在電影裡頭找光或為革命女子尋找她的光,私底下卻是為生活困頓中的自己找尋活著的能量和動力,因為作者發現了「我們坐著老去/但也不必即刻死去」的宿命,而老去死去的前提就是失去了光,沒有了能量,生命也就沒有了意義。
然則,對於作者,這光過於鋒芒,恆久不變,讓人發懅,卻不知如何以對。想把臉撇開之際,又偷偷顧盼一眼,心中道:那束光不就是以前追求的「瞳孔中曾經的光」,來自「某些深淨若海的歲月」?於是作者有了遮光的舉動,詩篇一開始的廉價傘便成了很好的工具,原來那不只是用來遮雨的,亦是當諸多青春回憶的化身返回經過身邊時不意中閃射出來的光,可以用這把傘遮掩起自己逐漸灰白的歲月,不讓其他人瞧見光照下青春不在的自己。
當「某些光/自壯年以後遠足,再也不曾回來」,作者自覺連革命的情感都沒有了,任何光都是一種刺眼的挑戰,她想迴避卻又不想示弱,一把廉價傘既成了防衛「年輕」與攻擊「老去」的最佳武器,亦是作者憂慮失去、怕被陌生人取走的東西。
至此,這道光顯然是因作者內心的黑暗,讓人覺得刺眼而帶點傷害。可是無可否認,光所照射之處都是美好的回憶,以及雄心壯志的未來;偏偏作者把「光會藏匿在/下酒的眼淚、蕭瑟的信件、偉大的呻吟」,讓這道光不只是代表明亮和能量,同時也承載了生命旅途中無法迴避的坎坷與悲涼。作者更設計了一場雨(肯定是南洋的滂沱大雨了),使光不是永遠地照射,遇上了雨天,電影中的革命女子就帶點悽涼,她為光(理想)而死,光卻不因此而復燃,至少不在作者心中,作者想逃避光,因為她心中的暗。如果拿我的一首詩來做比較──「衝撞溢流黑油的空屋/火苗會帶來死亡帶走黑暗」(〈灰燼如果自白〉),我寧可帶著光亮以飛蛾撲火之勢去燃燒自己,以求得四周更為明亮,不管老去死去以後的事情,不論在哪一段歲月年華。那麼,我的光亦將刺痛作者,讓他不得不趕緊拿出傘來遮擋了。
或許這只是作者一時之抑鬱所造成的黑暗期(對光暫時不能適應),正如詩篇最後「再也找不到開始。的那把傘」了,似乎洞見了一絲光亮,因為作者把傘移開,嘗試讓光自然照射進來,照亮持續放映的生活瑣碎──讀報、散步、修剪盆栽、回憶的一般日子。沒有光就做不了這些事。
二、光的照射方式:意象與影像的互攝。
接下來我要談這首詩歌的創作形式,文章起始已經點出整首詩的斷句和標點的特殊性。比如詩作一開始就擺出了「(撐一把廉價傘。的雨天)」──用句號將撐傘和雨天隔開,映入眼底即是兩個場景,傘跟雨天。再如「電影中某個革命女子,死了」裡的逗號將人物和狀態分開,「一起晾在案發現場。風」的句號則把動作和物分開,很明顯的運用了電影蒙太奇手法,一句詩分成第一幕和第二幕去完成。陳燕棣要讀者先看到的清晰畫面,先於詩句所要傳達的意涵,她給我們設置了一個場景──詩中電影之外的生活景況,我們就在她營造的這樣迷幻分不清虛實的時光場域裡展開尋找光的旅程。
對於學過電影、寫過劇本的創作者,在文字作品中融入電影語言是不經意且輕鬆自然的,而如陳燕棣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研究所,所學所寫無不與劇場、電影相關。這類創作者運用和掌握影像的鏡頭,就像詩人在詩中鋪成意境;他們捕抓的分鏡即是詩人想破頭經營出來的一枚意象。所謂意境就是畫面的感受與意義的傳達,詩歌的意境往往藉由對外在情景的融合以文字再現,而電影則是以影像和聲音。不同的創作語言/媒材形成不同的藝術種類,但是詩和電影是否有其交集,誠如上面所述,陳燕棣在此證明了詩是可以用影像(文字)來傳達的,而且影像躍然於紙上詩中,而又像詩一般返回到文字之美感,意象和影像成了絕佳的對照與互攝。意象中的語義本來就指向影像中的本事,如今作者將之翻轉,讓本事中的細節反指語意中的紋理,構成互為主體與客體的意涵交混(hybridity),讓影像補充詩中不足的意象成為主體,又讓意象解釋成為客體的影像,共同完成一個詩的畫面,讓詩也能用「看」的(不只是「讀」詩)。
這種形式並非獨創,小說創作側重情節,為使節奏緊湊,常會使用電影中的分鏡方式而不去完整敘述事件始末,讓讀者在第一幕的殘留影像中卻能馬上意會到第二幕出現的結果,達到了「不言而喻」的效果。但是在詩歌創作上能這樣「省略」鏡頭(意象)嗎?是否會影響我們對此首詩的感受力?陳燕棣沒有在此做出實驗,如果她做了,這首詩可能變成:
電影中某個革命女子
覆蓋她的僅是一條單薄褪色的布
風漠然揚著
她瞳孔中曾經的光
意象和意境仍能到味,但所述為何就讓人摸不大透了。
陳燕棣在〈光〉這首韻體詩(用辭淺顯,看似口語詩)示範了如何分鏡,如何讓電影蒙太奇手法補充詩中不足的意象,使讀者能由意象和影像去感受,互相牽引出一首詩的況味,這是詩人成功的地方。
順道一提口語詩的部分,就詩作發表的數量來比較,馬華文壇比台灣文壇更能接受口語詩。我所知道的馬華口語詩始祖要算游川和方昂兩位,其中游川能寫出兼朗的短詩,因為其「文字短,含量大,富於口語化,簡潔明快,一針見血,反諷深刻」(田思語),有時還加進各國語言和方言,一旦唸朗出來是氣魄軒昂、抑揚頓挫的,馬華詩人田思評之為「游川式」。例如〈當我死後〉假想自己死後的身軀要如何安排,將浸染不同文化裡的實體一一分割,「把穿蘋果牌牛仔褲的雙腿/砍下給美國/穿峇迪T恤的上身/留給馬來西亞/穿日本拖鞋的雙腳/送去日本……」,並且反覆自問這樣做是否合法,顯出詩人對於文化並不能代表國籍的嘲諷以及身處無根可循(多元文化交融)的國境的無奈,最終空留一個無主的靈魂。游川早期的詩作多有如此“破格”形式,接近口語自白,讀來亦有韻體詩的味道,在當年受台灣現代詩派影響下的馬華文壇可算獨樹一幟。
口語詩是現當代的中文詩歌創作形式之一,而緊扣口語詩寫作的即是如何將所見所聞所想直書出來,並且要扣人心弦(就算不用意象),所以詩人更加必須掌握電影語言和捕捉鏡頭的能力才得以藉文字在讀者面前開出一扇扇的情感畫面。
三、意涵的趨向:他們關心什麼?
這幾年我陸續讀到的文學獎得獎詩作,不論是在台灣和馬來西亞各大文學獎項,大多以一種生活化語言切入以往的偉大命題,如生命、死亡與超越。他們不再把生命寫得悲壯,革命可以不偉大可以半途繞跑,愛情不一定海枯石爛,超越自己也算不了什麼。年輕詩人們的價值觀已經改變,他們有了新體驗,另類的詮釋逐一展現在他們的文字當中。他們藉描繪生活中的細節來展現小情小愛小憂傷(小並無貶意而是對於命題份量的輕重之別),告訴世人他們可以這樣愛,這樣搞革命,這樣快樂地活著,不必像前人愛得死去活來,不必殉身成全革命事業。
台灣詩人陳雋弘在2002年獲得第二十五屆時報文學獎的新詩首獎〈面對〉,2003年馬華詩人冼文光則以〈一日將盡〉獲得第二十五屆聯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兩首詩的主題皆圍繞生活中小細節所引發的感觸,可以說是「小題大作」,將平凡不過的瑣碎事以顯微鏡放大與探測。僅以〈一日將盡〉為例,作者書寫即將入夜的房間裡兩個人的互動關係──鋪床、關窗、調校電視機、刷牙、換睡衣,然後躺在床上閱讀,回憶邂逅的日期、做愛的日子,再回到閱讀的文本,開啟理想生活的想望──「你是我/見過最偉大的作者,你是我/見過最真誠的讀者」。基本上書寫黃昏以後的作息,可以說平鋪直敘,而到最後閱讀、書寫與生活、身體交融合併,「鑽入/我的睡衣、我們的身體」。以往對待生命的那種英雄主義的崇高感在這裡被消解和淡化了,代之以一種醒覺的平民意識,形而下的事物與情感也可以不加修飾顯現出他們的美好。
陳燕棣則在〈光〉裡述說一個理想的幻滅,告別青春的尾巴,迎來不願去面對的「老去」。這些老掉牙的命題在當代詩人筆下仍免不了帶點哀戚悲涼,但隱然有種「輸了又怎樣」的豁達,遊戲性與耍賴的個性在描寫看一部電影外頭卻下雨的心境過程可窺一二,一個理想的幻滅居然是在電影院中開始與終結,散場後甚麼都不再去想。理想、革命、生命與死亡,已然不是當代創作者苦思探討的主題,而是輕描淡寫帶過的喟嘆,因為這些已經「沒有意思」(給廖宏強散文〈他鄉的故事〉一個解答)。
不管怎樣,當代詩人的社會意識與人文關懷的逐漸消逝是個不爭的事實。革命過的老了,老了以後過著安逸的資本主義生活,而那些血氣方剛的年青人呢?蕭伯納提供了一種說法:「一個30歲以下的年輕人如果不為馬克思所吸引,那就是沒有理想;如果過了30歲而仍然相信馬克思,那麼便是傻子」。更多後來的年輕詩人游於藝於網路空間,結社結派也只是一時,很快就拆夥走人,對周遭變化顯得冷感,卻在網絡空間尋找到刺激與新知,將創作空間進一步「虛擬化」,與現實文化有了分隔。或許也因為思考層面的降低,口語詩形式的自由狀態致使他們不再凝思結語,將所見所想投注在一首詩去爆發威力,而將其拆散作呢喃式的「自白」,削減了詩的力量,同時分散了關注的焦點。
當一切事物都消失了莊嚴與崇高的光環,還原到一個真正的存在世界或相對的網路虛擬空間,詩歌(文學)創作沒有了難易度,間接走上了重新定義的危險邊陲,再一次讓各方的謬思去平衡詩的純真意識(《壹詩歌》創刊一號宣言)。
結語:大影響,小焦慮
在台灣,前輩們用舊時代的美學創作觀像金箍(為什麼不是桂冠呢?)緊緊套在年輕詩人的額頭,好幾屆文學獎新詩作品飽受強者詩人的批判,反而忘了評選者該負起更大的責任;在馬來西亞,年輕詩人/創作者的作品獲得文藝副刊大篇幅的刊載,馬華詩人如過江之鯽,大家的機會都是平等的。在大陸,每隔一個世代的先鋒詩人藉著論戰奪權,成為詩壇的中堅份子幾乎是傳統了。
普遍上,年輕詩人一方面嘗試新語言與新創作態度,一方面卻因為不被前輩詩人接納進入詩壇而懷疑起自己的創作方式。更多年輕詩人未能夠掌握自己的詮釋權,他們像遊俠兒往來於各式創作媒材,游擊般到處「玩」創作,可以說是文壇狹隘毫無包容力,其實彰顯了有太多詩人/創作者面對詩歌與創作時,永遠會有一種處於懵懂無知的狀態(不知道自己在寫什麼的大有人在)。
美國文學批評家布魯姆(Harold Bloom, 1930~ )指出,若要走出前輩詩人的陰影,就得拋開歷時性的束縛,也就是超越歷史和時間進入純文本性比較。對於這種比較,後來詩人和前驅詩人的作品實際上都不是獨創的或獨立的「詩」,它們只是各種前人的「詩」的文本的交叉體現(intertextuality)(《影響的焦慮》,江蘇教育出版社,第四頁)。如此一來,當代年輕詩人便可以消除心中焦慮,至於未來怎麼寫、寫什麼,不妨用各種方式去「誤讀」和「修正」我們的前人,亦即貶低我們的前人(布魯姆語),從而樹立我們自己的風格來與之抗衡。陳燕棣即用自己的感知去重新詮釋理想、革命與生命,但是(私底下)我覺得她不是為了在文壇佔有一席之地,亦不想樹立自己的風格,她只是「無聊」所以「無以名狀」寫了詩。
下一個太平盛世,詩人會用什麼武器來反射詩之靈光?希望不是消極的運用廉價雨傘來遮蔽,倒不如考慮太陽能板眼鏡,因為除了可以隔絕紫外線,還能把光能儲存起來,或許隔了一層鏡片,看的東西就會不一樣,世界會顯得美好。但是,請不要忘記,我們瞳孔中曾經出現的光,不管是先來後到,現在和未來,依然照射遠方,在那裡互放著光芒。
附錄:
光
陳燕棣(撐一把廉價傘。的雨天)
電影中某個革命女子,死了
覆蓋她的僅是一條單薄
褪色的布、和著觀眾的嚼食動作
一起晾在案發現場。風
漠然揚著。爾後泥土也無法辨識出
她的年代(右侵的脊椎、憂患的掉髮、翻過歷史的指紋)和瞳孔中曾經的光我們遇見她和自己
的光。好久,不見生之所及,光會藏匿在
下酒的眼淚、蕭瑟的信件、偉大的呻吟
以及,遇見老詩人的街角
諸如此類,如此瑣碎的其間
但一般時日,我們不常和它相遇我們曾經虛無壯烈(如革命志士)
和她一樣天真(也無知),揮汗,把星暉懸於嘴角直到現在,革命
女子的落寞,比我們落寞
她難堪(某些光
自壯年以後遠足,再也不曾回來)
聊勝於我們的貧瘠
我們逐漸乏味,傾向
苦澀。唯有選擇讀報、散步、修剪盆栽或者
安靜的(在回憶中)游泳。也或者
看一些電影。以為足以從中
逃走。然後某個停格也被光
刺中。繼而想念──
然後苦笑連同爆米花可樂(其實
我們並不飢餓)和
打嗝、呵欠、哀悼女子自殺
我們坐著老去
但也不必即刻死去(因為──
怯懦如我們,並不革命)女子帶走光(某些
深淨若海的歲月)我們不找
光(黑幕緩降,背後有
生活持續放映)。僅是憂慮著
放在門口的傘,是否
已被路過的陌生人蓄意拿走當瞌睡熬到終局,沒有掌聲響起
散場了,身邊有文藝青年
三個、五個、成群結黨
走過(穿越我們的灰髮)
我們卻被光(麻痺軟弱的步履)
絆倒。沒有掌聲
響起(再也找不到開始。的那把傘)
詩作原刊登於《星洲日報》「文藝春秋版」(05/08/2007)
[ 點閱次數:15819 ]
/ 木焱
1996後旅台馬華文學的在網路化
我很早就在副刊上注意到邢詒旺的詩,早于他獲得花蹤文學獎,早于他出版詩集。如果沒記錯,那時他剛留學台灣,而我已大五畢業。若以旅台馬華文學史來歸納,邢是在我們(木焱、羅羅、龔萬輝、劉藝婉、陳耀宗、顏健富、張瑋栩)之後,而和劉慶鴻、蘇怡雯同屬一期的旅台馬華創作者(目前所知旅台的年輕創作者有林明發和謝明成,前者寫小說,後者寫詩;其餘還逗留在台,或工作或唸研究所的馬華創作者亦不在少數),那時網路發表平台已經不只是bbs的天下,還有明日個人新聞台(已更名為Pchome新聞台)、phpbb介面討論版、部落格,甚至撰寫及成立個人網頁亦非難事了。創作者因而擁有更多(元)的發表空間,但卻因為平台的氾濫(開設更多獨立個人網頁)而始終凝聚不了更多網路創作者以進行交流(除非善於營造網路社群,製造話題來刺激點閱率,否則很難吸引他們,更妄論留住。此網路社群議題早有台灣學者著述探討,讀者可上網搜尋閱讀),不若1996至2000年期間,我們不約而同的彙聚在大紅花的國度、田寮別業等bbs站的現代詩版(以貼現代詩為主,並設有精華收藏區或個人版)討論分享的盛況(許多旅台文學獎得獎人多在其間竄流,po文章,re文章)。
以上我大略回溯邢詒旺之前以及他後來所處的創作與發表機會的情況。
2002年四月,邢在Pchome開設其個人新聞台〈乾爽地帶〉(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tendernest),截至現在發表文章已達260筆,幾乎都是現代詩作品,還有幾篇讀詩筆記;而每個月至少會發表兩篇文章,可見邢的用心經營。由此可見,網路不只是具有無國界的發表平台,這個平台亦是作者「放置」作品的藏詩閣,可以搭配圖片甚至做成電子書,而增加點閱率的目的性反而顯得不那麼重要了,文字創作者設立網頁主要是想讓其出版品的讀者和朋友有個聯絡的「方式」(some-way),但近來這種態勢已逐漸被部落客(blogger)翻轉,經營網路創作平台的熱度再度浮現,與平面媒體並駕齊驅,端看台灣中時電子報舉辦的全球華文部落格大獎的盛況可知一二。
諸如許多創作者最終渴望的是在平面媒體如副刊上發表,邢在留台時便已頻頻在馬台港等地的副刊和詩刊雜誌發表詩作,詩質受到編輯們的檢視與肯定。盡管和同期旅台馬華創作者的交流機會受限,然而邢卻因為身在中文現代詩的大本營──台灣現代詩壇,得以吸取廣博的文學養分,學習與成長;在他獲得第7屆花蹤文學獎詩組佳作之後,發表在馬兩大報副刊的篇數更是直線上升(可見文學獎對於一個創作者是何等必要)。於是,邢詒旺在詩的孤獨國繁衍眾多詩篇,眼下這一本《戀歌》就是他的第二顆結晶體,而主軸比上一冊《鏽鐵時代》更加清晰,結構乃14行,外加兩首長詩;詩想乃自我的砥礪及提升,我們從輯名便可探知一二,故地有泥-漫行-山訓-換弦-望川-……-來雲,串成了一幅詩人追求自我的心情風景。
現代詩與十四行
說到十四行詩(sonnet,此種嚴謹格律的詩體)是否到了當代還要依循其排列的句數為4-4-3-3或4-4-4-2,文學史早已有所記載:十四行詩有固定的格式,它由兩部分組成,前一部分是兩節四行詩,後一部分是兩節三行詩,共十四行。每行詩句通常是11個音節,抑揚格。每行詩的末尾押腳韻,其排列方式是:ABAB﹐ABAB﹐CDE﹐CDE。它和歌謠、抒情短歌同為當時義大利抒情詩中流行的體裁。當十四行詩傳入法﹑英﹑德﹑西諸國,並適應各國語言的特點,產生了不同的變體。而詩歌發展至現當代,已不在講究規範(因為現當代詩就是要打倒詩的規範),所以詩人可以隨意安排詩句段落,只要不超過14行,都可以當作十四行詩(一種仿冒嗎?詩人自陳仿冒一些傳統形式,試圖接近、體驗、印證一些什麼)。所以邢的十四行詩是sonnet亦非sonnet,那是詩人的擬真(一種復古?邢把此舉當作是形式和內容的顛覆,遂運用了後現代的概念把「顛覆」詮釋為「重複」或者如他所說的「仿冒」),是詩人給自己設下的一道題(一種對傳統詩體精神的延續?),將詩意控制在14行裡面,他隱藏了莫名意圖,目的是要我們讀到詩篇如何精彩。
輯一主要在自我定義,我們讀到詩人如何定義他的「愛恨與羞恥」,說明他的「不應該」和「愛總是」。此輯最好的作品勿庸質疑是〈故地有泥〉,乃詩人對待生于斯長于斯的故土的一份感恩,有種近鄉心怯的懷想。輯二打開視野,我們讀到詩人觀照四周環境的嬗變,看潮水的起落,風纏繞著腳的漫行,印度的sari像海水,都是他獨有的觀賞角度。到了山訓一輯,詩思有了高度,雖是進入山鎮受訓兩日所寫,卻可見到詩人的靜思,進一步探測內心的向度。例如「那煙霧,是一團/樹的吐氣」、「山在哭——人口/從大貝殼中排出」、「我感覺全身破碎,仿佛破碎的全身/是我的愛」,可惜後面幾首如〈是我〉、〈斷章:無奈〉、〈山外〉卻亂了分寸,思想脫序。換弦一輯主要寫物,語言上有意開創新格局,如「日月撞擊,互逐/如磁丸——巨物/的下體,啊/使我閉上眼睛,默默/忍受。腐朽的蘋果」(〈紅塵漸漸〉),外在與自我的懸殊比對,但又抓住了詩意的連貫,這種特別的處理在此輯內不難看到,但是整首詩的連續性仍有欠完滿,因為當形式先於內容,突顯了詩的語言卻容易丟失了主題(內涵)。不過我仍舊欽佩邢的大膽開創,寫出「如一枚斷裂的北斗在黑河漂浮/不曾離去不曾舀唱過任何一種完全」如此的句子,顯現其特有的美學觀,假以時日不難寫出純熟的個人風格。另外,〈我聽見茅草〉和〈燈〉都有不錯的表現。
短詩貴在靈光一閃,長詩貴在敘事結構,十四行詩不長不短,意象與意境的鋪成受限,敘事結構亦受箝於行數無法開展恢弘氣勢,更甭說把靈光拖沓在14行裡面分散閃射,這詩難寫,邢有意挑戰(是否能解釋古今西方詩人屢屢嘗試寫十四行詩的意圖呢?)。晚近德語詩人里爾克遺留下幾部經典的十四行詩集《時間之書》、《杜英諾悲歌》、《給奧菲斯的十四行詩》,倒是讓讀者在選讀著名的莎翁十四行詩之外有不一樣的美學感受。再拿邢詒旺這冊十四行詩集,讀者不妨參照比對不同世代的創作風格,或許可看出文學和思想演進上的歷史刻痕。
新生代詩人的口語化形式
爾後的輯裡,內容或觸及詩、詩人、政治、天災人禍和心情轉折等等生活書寫,邢有意無意地運用口語化的自由詩體(free verse),讓我們也能聽到他的另外一種「說話」方式。口語詩在新生代詩人的位置,正如中國新詩學者陳超所言:「(中國新生代詩人)在很短的時間裡「共時」親睹了一個相對主義、多元共生的現代世界文化景觀。在意識背景上,他們強調個體生命體驗高于任何形式的集體順役模式;在語言態度上,他們完成了語言在詩歌中目的性的轉換。……新生代詩的主脈之一「口語詩」卻更多地意識到,「你自己」只是一個小小的個體生命,不要以「神明」自居(包括不要以英雄、家族父主及與權力話語相關的一切姿勢進入詩歌)。」(《中國先鋒詩歌論》,陳超,pg.5)這種情況在港台、馬新等新世代詩人(1971年以後出生)亦如此,盛行於90年代末尾至今,而成為新新世代詩人(1981年以後出生)的主要表現形式,從韻體詩到口語詩,這批年輕詩人潛意識運用平民化書寫,淡化歷史和文化,消解文化,切實地進入到現代詩的實驗,還原了人和詩存在的本真狀態。
大陸先鋒詩歌於90年代崛起,其中代表人物于堅、韓東、歐陽江河,以口語詩告別了上一代的朦朧派。晚近的朵漁、李紅旗、沈浩波,更是發起「下半身寫作」來回應中國的傳統詩歌界,引發大陸先鋒詩界民間立場和知識分子寫作的大論爭「盤峰論爭」。當代大陸先鋒詩派所提倡的,詩人首先是人,然後才能談得上詩;詩首先應該是一種返歸到平凡人世界的生命形式,然後才是文學。如此的論調盛囂直上,年輕創作者亦多有認同,不可否認的是形而上的崇高思維已經在找尋她形而下的肉身,並藉此肉身說出「自己的歷史」。
口語化書寫在新生代詩人之間迅速被接納,借助網際網絡的普及,電腦書寫的快速與文章發表的分行習慣,使得任何一段文字都先具備了詩歌的「模樣」,加上口語詩所確立的文學位置,造使一封電子郵件或廣告文案或分行文章都能解讀成為一首口語詩。詩歌(文學)創作已不知不覺下放到平民化水平,假使我記錄下某一人的講話內容,分行寫出就是一首詩,遂成「每一個人皆是詩人」(前衛藝術家波依斯曾提出「每個人都是藝術家」的觀點)。然而自覺有創作能力的寫詩人,為了跟「每個人皆是詩人」的人區別開來,趨向把生活化的口語轉換成個人主義的表徵,把自己獨見獨想大剌剌地直抒出來,不論是好的壞的,舉凡白日夢、無聊、日常活動、嗑藥、性都是他們喜歡書寫的題目,然後「巨細靡遺」(可以是逼真的虛構)的寫出(告白),私底下各自較勁誰的生活精采,誰的「詩」最勁爆,卻模糊了文學性與藝術性。
因此,文本不再存有被詮釋的意義,評論家不能再用文學理論(而是以文化研究的面向)去評價這些作品,因為創作者把自己無限放大,將他自己(生活的空間)直接投射進「詩」的模具內,這些文字的意義是直接指涉創作者的生活,不會有多餘的涵義,有的話也可能是評論者或讀者從自己心靈感受出來而非作者意欲表達的。如此說來,詩壇的存在就是來篩選與界定詩和非詩(他們又是如何去界定?),免得一概文字魚目混珠,把小說當作詩,把夢話當作詩,把廣告當作詩。所以,年輕詩人屢屢想打破詩壇的獨霸與逃脫前輩的陰影,卻因為不加思索地接受過于開廣的藝術形式而賞了自己一道耳光,登上的文學道路馬上又打了包票退回原點。
在此,我並不否定口語詩具有文學性和藝術性,端看它所處的文學歷史背景及其發生的緣由;藝術形式和美學理論不是憑空冒出,它們一定和所處世代與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果硬生生借用外來的創作形式,就像只吃到好味道卻不知道吃的是什麼東西,永遠只能說好,卻不知道好在哪裡。新新世代的詩人須借鏡於此,開創屬於自己那一代的創作風格,讓文學得以往前行走而不是原地踏步,更不能對外來種照單全收。
繾綣戀歌
當「琥珀把詩人定位/成為時間的飾物」,我們讀到詩人的長篇巨構。〈一個青年病患家的畫像〉題目改自喬依斯自傳體小說《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自畫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全篇分作四首詩來處理,長短不一,對生命和死亡、存在與消長進行一番審視,有別於前部十四行詩的「淺嚐即止」,他不急不徐的經營意境,在韻律節奏下了功夫,斷句也恰到好處,讓人讀到生命的細細長流,品味再三。不過〈戀歌〉更顯成熟,不論詩藝和內容上,邢都運行自如,細微的觀察與唯美的意象轉換是這首詩的成功之處。在這首長詩裡,邢不再使用雲、雨、雷、風的意象,他進入到自我的思維空間,譜出「如情人的齒痕輕輕印在/記憶的嘴唇?起初是驚恐/甚至震怒,然後汁液流出/從那果實的缺口,我們品嘗到了/自己所無法開啟的」(〈嬰孩一〉),語言新穎,思想沉著。諸如此類的精采篇章俯拾皆是,請接下去讀:「回歸靜默。再一次,你的甦醒/像一隻貓咪信步來到郊外/使斑斕的花蝶面臨斑斕的扑/滅。花蝶,部落,我們都活在/一瓣,一葉或一翼的某一點上」(〈嬰孩二〉)。又如他描寫生命與死亡的關係,成熟中透露的慧黠:「那些我們稱之為經驗的屍體/其實和我們一樣,是漂浮/也是固定的:你邁向死亡/帶著歡欣和恐懼像郊游的貓/撲滅:我們是你斑斕的夢」(〈嬰孩二〉)。如此說來,〈一個青年病患家的畫像〉要算作是〈戀歌〉的練習發聲之作,〈戀歌〉的結構完整,情感連貫,意境連續,也不再炫技(詩人在此已掌握詩的技藝),我覺得是本詩集最精采的作品了。
如果真要挑剔,很明顯的詩人的耐力不足,寫長篇韻體詩尤其考人耐力。邢在這兩首長詩裡數度以()內的自我呢喃為詩寫的瓶頸開解,或以反复、排比的口語來發洩靈思的枯竭,如果把它當作詩人的風格化語言未免牽強,一首長詩最忌諱的就是「暴走」的奇想(或因受困的思想而引發),當詩人按壓不下來時,通篇辛苦建構的語言風格就會出現不協調的景觀而毀於一旦。如果邢能通過這項考驗,修行得道,以平常心看待,便進入到另一層詩歌的狀態──所謂生活與藝術的對話,詩藝與思想的融合,最終將詩和人結合在一起。
零度的風景──詩歌的純粹
無疑,這本詩集讓我們讀到詩人正在修行自我,他日成為金剛不壞之身。不管是仿冒或者擬真,那些都只是詩歌/美的表皮(所以才有那麼多流行文化)。詩人在自序中寫道:「寫詩一段時間,難免會搜尋起詩的本體、原因、可能、目的,及其他。」我迫切期待詩人那種強大的自覺力量最終衝破文字框框的結果,那不再是「暴走」而是「破繭而出」,或者用被動的說法「水滴石穿」更為貼切。當文學被衝破了,是否意味著詩歌的宿命,即詞的流亡(北島語)。那時候,詩會是這樣的風景呢──
是鷂鷹教會歌聲游泳
是歌聲追逐那最初的風
我們交換歡樂的碎片
從不同的方向進入家庭
是父親確認了黑暗
是黑暗通向經典的閃電
哭泣之門砰然關閉
回聲在追趕它的叫喊
是筆在絕望中開花
是花反抗著必然的旅程
是愛的光線醒來
照亮零度以上的風景 (〈零度以上的風景〉,北島)
還是其它?我們屏息且拭目以待。
(全文刊登)
預告:從門縫裡引進一道光
──談陳燕棣的詩作〈光〉
《字花》2-3月號
[ 點閱次數:15244 ]
作者:楊宗翰 台灣佛光大學文學系博士候選人‧玄奘大學中文系兼任講師
寫詩,讀詩,評詩,玩詩。關於詩,還有什麼愛詩人不可不知?關於交流,不可不知詩社與詩刊;關於閱讀,不可不知詩人的網站;關於投稿,不可不知全國或區域性文學獎。
詩社是情感或理念結合下形成的團體,詩刊則為詩社同仁執編與發聲的園地。台灣詩壇也曾出現過極少數「非同仁詩刊」,可惜壽命不長且影響有限。晚近台灣同仁詩刊對外稿的態度都相當開放,就算面對其他詩社的要角來稿也少有門戶之見,自認有滿腔詩血亟待發表的文學青年大可一試。坊間報紙副刊在讀者數量上雖壓倒性地遠遠勝過詩刊,但副刊編者為顧及多數讀者偏愛娛樂性較強的「中額」(middle-brow)之作,對前衛詩篇往往避之唯恐不及。詩刊的讀者卻是另一種人——自認也甘於是「小眾」、對主導文化裡的中產作品基調深感不滿、對另類手法與實驗企圖懷有期待——故樂於擁抱各式各樣前衛詩篇。詩社與詩刊讓這群「小眾」有機會聚在一起共同取暖、交流詩心。據張默《台灣現代詩編目(一九四九~一九九五)》書末所載,台灣「當代中文新詩期刊」凡十四種,既有老字號的《現代詩》與《創世紀》,也有甫創刊的《植物園》及《雙子星》。十年過去了,《植物園》、《雙子星》早已夭折,連最具歷史象徵意義、曾領導戰後新詩走向的《現代詩》都再度吹起熄燈號(按:紀弦主編的《現代詩》出版至第四十五期後停刊,梅新等人自一九八二年起復刊《現代詩》,現亦停止出版)。今日詩壇最有活力、最具代表性的幾份刊物如下:
一.《台灣詩學》:
一九九二年創刊迄今未曾間斷,自四十期後增加新詩評論質量,改名為《台灣詩學學刊》。成員多具學院派色彩,既能寫詩亦能論詩,可說聚集了中生代最銳利的幾枝健筆。該刊歷任主編白靈、蕭蕭、鄭慧如皆長於策劃,從早期之「大陸的台灣詩學」到晚近「現代詩與現代性」,每期專輯皆頗為可觀並引起不少討論。值得一提的是,該刊在網路上成立了「吹鼓吹詩論壇」,實施投稿與論壇合一制,凡網路投稿必經多次篩選後方予刊出,同仁並會針對獲刊作品撰寫評析。此一設計有效結合了網路與平面媒體資源,對獲得刊出機會的年輕詩人亦深具鼓勵與指正作用。
二.《現在詩》:
二00二年創刊,由夏宇、鴻鴻、阿翁、零雨輪流主編,每一期的主題或設計都讓人充滿驚奇:刻意穿孔、必須一頁頁撕開來讀的第一期;全身粉紅、貫徹「來稿必登」理念的第二期;聲稱編選原則是「絕對主觀」的第三期;還有預定今年底出版的第四期「行動詩學」……。標榜「現,就是行動/在,就是發生/詩,就是詩」的《現在詩》,每期出刊都宛若一件觀念藝術的誕生。
三.《壹詩歌》:
二00三年六月由可樂王、木焱等青年作家創辦的《壹詩歌》,不時可見詩歌、圖像與音樂三者的跨界色彩。閱讀這份由寶瓶文化支持的「獨立文學雜誌」,會覺得封面與內頁照片讓此書貌似時尚刊物,在華麗的包裝下卻又潛藏許多年輕詩人大膽的詩創意。雖然編輯群在生理年齡上至少差距一代(十歲),《現在詩》及《壹詩歌》卻同樣具有前衛色彩,也都似乎有意告別傳統老牌詩刊的菁英傾向。這兩份新興刊物無疑是指向世俗與庶民的——但願這個俗世能容得下他們,以及他們內在的革命意圖。
四.《創世紀》:
一九五四年面世的老牌詩刊,其間曾短暫休刊,復刊後更見精猛。去年秋天歡度五十周年,出版了一冊厚達四四0頁的紀念號,堪稱台灣詩刊史上最大規模的製作。《創世紀》致力於詩創作水準之提升,亦儘量提供最多篇幅來刊登詩作;相形之下評論部分稍弱,擅於長論的同仁張漢良與葉維廉惜墨如金,幸有簡政珍、游喚等學院出身作家勉力支撐。雖為同仁刊物,但《創世紀》園地還是相當公開,無論對大陸來稿或台灣未成名年輕詩人都相當友善。在外稿無虞、同仁創作又一向質量兼具的情況下,《創世紀》比較大的問題或許就在成員新血不足、年齡偏高了。
五.《笠》:
同為老牌詩刊,創立於一九六四年的《笠》在補充新血這方面比較積極,晚近加入的幾位「六年級」詩人在創作上已有不錯成績。《笠》的編輯策略較趨保守,但在對外交流與文獻翻譯上一直很有貢獻。從前人們常認為《創世紀》與《笠》一為外省軍旅詩人的集結、一為本土派詩人的團體;其實這只是早期成員的身分色彩,而非今日他們選詩及刊詩的標準。維持園地開放、容納年輕異音,正是這些老牌詩刊值得敬重之處。
六.《藍星詩學》:
前身也是老牌詩刊的《藍星詩學》,由淡江大學中文系負責支援編印工作,該系教授趙衛民擔任總編輯。《藍星詩學》重新集合了幾位「藍星」詩社大老與中生代詩人,每期皆規劃同仁特輯為其鮮明標誌與特色。所幸這樣的編輯策略,尚不至對外稿產生太多排擠效應。惟創刊於一九九九年的《藍星詩學》(季刊)自二00四年新春號後迄今仍未見新刊,前景令人憂心。
七.《乾坤詩刊》:
自一九九七年創刊以來一直穩定出版面世的《乾坤》,是詩壇唯一一份同時刊登古典詩詞與現代詩篇的刊物。近幾年該刊編輯群普遍年輕化,在編排及封面設計上蓄意革新,並與金石堂書店合辦「詩生活講座」弘揚詩教,用心與成績值得肯定。
八.《當代詩學》:
二00五年四月創刊的《當代詩學》並非詩刊,而是台灣第一份純粹「詩學研究」刊物,只登詩論、不刊詩作。《當代詩學》由揚智文化與國北市台文所合辦,第一期為「兩岸詩學專號」,第二期則預定推出「台灣當代十大詩人專號」,並將辦理十大詩人選舉。新生報到,前途難卜。
對網路世代來說,詩人網站是他們認識詩最好的地方。誰說老人不飆網?資深詩人向明與張默可都有「個人新聞台」!中生代詩人則更進一步發展數位詩,從蘇紹連的「Flash超文學」(http://myweb.hinet.net/home2/poetry/flashpoem/index.html)、須文蔚的「觸電新詩網」(http://dcc.ndhu.edu.tw/poem/index01.htm)、白靈的「象天堂」(http://www.ntut.edu.tw/~thchuang/e/index.htm)、向陽的「台灣網路詩實驗室」(http://home.kimo.com.tw/poettaiwan/)上都可以找到許多數位詩創作。至於時下最受人矚目的部落格(Blog)則是年輕一輩詩人的最愛,從「台灣網路詩人部落格聯盟」(http://blog.yam.com/taiwan_poem)可以連結到近百戶詩人部落格:阿鈍、鯨向海、紀小樣、楊佳嫻、kama、曾琮琇……。值得注意的是,年輕詩人中擅長以Flash或Java創作者似不多見,反倒是中生代詩人在這方面功力深厚。此外,不可不提以會員論壇形式經營有成的「吹鼓吹詩論壇」(http://www.taiwanpoetry.com/forum/index.php)。這個由米羅‧卡索(蘇紹連)負責維持的網站,兩年內聚集了兩千多位註冊會員、共計發表超過兩萬篇文章,論影響力與活力絕對不在其平面傳媒母體《台灣詩學》之下。
對喜歡詩創作的人來說,文學獎既是誘惑,也是刺激自己進步的動力。台灣各式大小文學獎眾多,且除了少數區域性文學獎會限制作者需有該地戶籍(或需以該地風土民情為題材),一般都是對外開放的。這也讓台灣詩人有機會跟新馬、港澳及中國大陸華文作家一較高下。全國性的文學獎多由大報副刊主辦,如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自由時報新設的林榮三文學獎;區域性文學獎則有台中市大墩文學獎、苗栗縣夢花文學獎等。以往因為獎金數與受關注度皆相差懸殊,有些讀者或創作者遂對區域性文學獎懷有偏見,甚至連帶輕蔑起得獎者來;殊不知區域性文學獎中臥虎藏龍,豈有小覷之理?至於有志進攻海外者,已舉辦過兩屆的「彭邦楨詩獎」也是不錯的選擇。其實,寫詩得獎或不得獎都是偶然,讀一首好詩、寫一首(壞?)詩才是必然,最最過癮的必然啊。
(原刊於2005年9月7日,自由時報‧自由副刊)
[ 點閱次數:1709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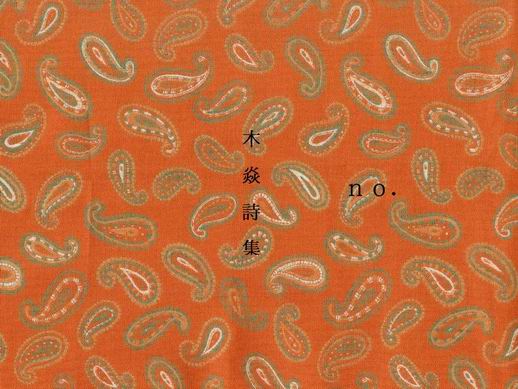
讀木焱詩集《No.》
木焱,我認識。就是BBS上的muyan嘛。
後來又認識了林志遠,他的詩〈2〉收入《八十七年詩選》裡,以一個理工科學生奇特的二進位邏輯和數字妙喻,令我印象深刻。
然後我認識了馬華詩人木焱。
那一陣子我很迷馬華文學,起先是接觸到美籍馬華女詩人Hilary Tham的兩本英文詩集Men & other
strange myths和Tigerbone Wine,以及她的散文自傳:Lane with No Name: Memoirs
and Poems of a Malaysian-Chinese
Girlhood。再來讀了黃錦樹的《馬華文學與中國性》、王潤華的《華文後殖民文學》,還有發憤閱讀但半途而廢的李永平大部頭小說《海東青》。我又千方百計買到了原甸的《馬華新詩史初稿(1920-1965)》、後知後覺的發現柏楊早在1982年就編過一套《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又讀完了陳大為的詩集《再鴻門》和《盡是魅影的城國》。然後往歷史溯源讀了李慶年的《馬來亞華人舊體詩演進史》裡介紹的海外竹枝詞。接著發現近年的論著真是源源不絕,黃萬華的《新馬百年華文小說史》、饒芃子主編的《中國文學在東南亞》、張錦忠的《南洋論述》。語言學研究也有李如龍主編的《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鄒嘉彥、游汝杰
編著,《漢語與華人社會》等等。而且幾乎每年都有可觀的碩士論文發表,例如:李志賢,《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歷史課本之分析(1975-1999)》、謝小鳯,《從社會語言學觀點探討馬來西亞英語之本土化》等等。至於馬華詩選,自陳大為、鍾怡雯主編的《赤道形聲》後,才不過兩三年,又出了《有本詩集》一大本22詩人自選。
不過,我以上拉扯了那麼多,其實只是想說:這些和木焱、木焱的詩完全沒有關係。木焱的詩呈現他本人,他本人呈現木焱的詩。
關於馬華背景,我確實曾經認為,正因馬來西亞的教育政策壓抑了華文文學,正因許多馬來西亞留學生以台灣的幾個都會、幾所大學為認同的中心,所以馬華文學似乎呈現出某種「時差」的感覺。好像那邊與我們這邊雖共享同樣的「時間」,但那邊的「時間」比我們這邊慢,好像那邊仍停留在我們1980年代那種有種種悲情和革命理想的美好時代。好像正因馬來西亞留學生在台灣人生地不熟、不易打入本地學生的圈子、打工賺錢不易、缺乏申請信用卡、助學貸款等金融手段、還要承受台灣都會較高的物價水準等等,使馬來西亞留學生並沒有沾染上近十年來我們這邊年輕人的物質消費狂熱。我曾經理所當然的以木焱《秘密寫詩》中的〈年代〉來證明上述這種頗為誤謬的想法,認為這造就了木焱那種遊俠式的、從下往上睥睨台北的、爾偶會ㄎㄧㄤ一部腳踏車或A一本書的特殊性。
不過,我錯了。木焱就是木焱。沒什麼好研究的。別用什麼社會學去分析,別想從他身上找到歷史線索。
我想,就算木焱用英文寫作、用馬來文寫作、用泰米爾文寫作,無論什麼文寫作都好,只要他願意說給在台灣的我們聽,我們所感受到的,仍會是同一個木焱。就像我讀Hilary
Tham的詩,雖然我的英文不夠好,但我仍能感受到她幼年時那南中國移民家庭的氣氛,仍能感受到她祖母,與我過世很久的「阿祖」(我年幼時都這樣用台語稱呼我母親的祖母),有著某些說不出的類似特徵,而深深引起我的共鳴。人和人,是一樣的。而木焱願意讓我們看到他。
具體的談一談木焱詩集《No.》裡的幾首詩好了:
[26]
如果有一條繩子
被用來包裹航空郵件
那一定是我的腸
所以我變得更瘦了
腸是人類最長的器官,扯出來長達好幾公尺,中文說肝腸寸斷,這首詩暗示出的思念之苦,正是如此。戰爭電影若要強調殘酷,常常製造出肚破腸穿,士兵捧著一團自己的腸子踉蹌呼救的畫面。
或是敘述日本武士切腹的小說,冷冷地寫著,第一刀割開肚皮,讓腸子垂露出來等等...例如,森鷗外(1862-1922)的小說〈堺城事件〉中的敘述:「箕浦開始鬆開衣服,將刀口由外朝內重重地插入左腹,然後往下割三寸,接著刀子向右拉,最後再朝上拉三寸,由於刀子深入腹內,故傷口相當嚴重。箕浦丟下短刀,用右手抓出腹內的大腸,怒目瞠視地面對法國人。…其中柳瀨將刀從左腹刺入拉到右腹時,又從又腹回頭往左邊拉,因此腹內的腸子從傷口溢出。」腸,是一個我非常不願意去想的器官,所以,我從來沒把綁包裹用的紅塑膠繩想像成是一團腸子。這並不是說我缺乏寄航空包裹給遠方親友的經驗,事實上,我童年回憶中重要的部分就是隨母親到郵局,寄包裹給移民巴西的阿公、阿嬤(外祖父母),所以很能體會那種冬寄毛衣、夏寄春茶的感覺。(當然,巴西的季節與台灣顛倒)
長大後,倒是常常寄各式各樣的書給朋友(常寄到澳洲,又是個季節顛倒之地),不過是印刷品,用不著繩子綑綁,所以漸漸就忘了郵局裡有一團繩子,會鈎起人們的愁緒…
下面首詩是電腦時代特有的sensibility(感覺力?):
[16]
按著enter不放
會有墜落的快感
和
探求不及的哀傷
電腦鍵盤上的enter鍵其實語意頗為奇特,一方面是「輸入」、「進入」沒錯,另一方面卻是「換行、「排除」和製造空白。能從按enter時電腦螢幕的畫面,聯想到「墜落的快感」,從一直下向用空白排除了字句,聯想到「探求不及的哀傷」,的確是很有氣魄的「感覺力」!
[30]
看看自己吧
不是要去看電影的嗎
卻賴在家裡打掃
打掃昨夜多出來的慾望
和以前激情下的落髮
對塵埃過敏
對工作感到沒有興趣
其實是害怕
賴在家裡害怕
把狗關起來了害怕
半夜被蚊子騷擾害怕
夢見你害怕
我覺得這首詩可以與另外兩首聯在一起讀:
[76]
我很害怕就這樣活
被你們研究
我的一生住滿蟑螂
一些沒用廢紙
當我發現
又得整理
[8]
廁所裡有一根頭髮
盥洗盆有一根頭髮
杯子裡有一根頭髮
妳嘴裡有一根頭髮
歲月啊有一根頭髮
卻不知道掉在哪裡
感覺上,木焱是個很愛乾淨的男人。雖然說《No.》這本詩集在我看來跟「私小說」的概念差不多,可以稱為木焱的「私小詩」,但我仍不至於蠢到相信詩裡的每一句話;不過若論批判性的閱讀,我還是可以抓到一些不經意的語氣,例如「當我發現/又得整理」,我想,這絕對是很愛乾淨,常常打掃的人,才會脫口而出的抱怨吧?
說到「私小說」,我承認我最近在看柳美里的《男》,在我看來,這本書介於「後設小說」與「筆記小說」之間,也可以視為「機智(或勵志?)散文」,我個人則當它是某種「體質人類學報告」。《男》的最後一頁,柳美里總結式地寫道:
如果要我描寫男人,我考慮以神話式的存在讓他上場。男人的面孔、性格、肉體都必須充滿神話性色彩。西裝筆挺走在都會中心的商業大樓之間,強壯的肉體兼具狂暴、狂野與知性……可是現實生活中,我所交往的男人偏偏都是肉體與精神完全靠不住的類型。我懷念那些離我而去,擁有眼睛、耳朵、指甲、臀部、嘴唇、肩膀、手臂、手指、頭髮、臉頰、牙齒、陰莖、乳頭、鬍鬚、腳、手、聲音、背部的男人。
事實上,這本書就是按照:眼睛、耳朵、指甲、臀部…背部,一章一節地用女人的情緒檢視著男人的身體。而我讀木焱的詩,有時也會有同樣的感覺,也就是感覺到木焱對身體的關注,感覺到那種「視線」。這可能是因為我自己寫詩的時候,越來越傾向把身體隱匿起來,物質化的傾向越來越重,或是關注虛幻的概念或靈魂,所以格外感覺到木焱詩裡面的身體。不過話說回來,木焱寫的畢竟是詩,他不會不厭其煩地描述各種細節。所以關於「頭髮」或「害怕」,能在字面上看到的也僅有「頭髮」和「害怕」而已。30號詩裡面打掃散落的「頭髮」的場景,本該激起一些意淫的偷窺感,但是加上了「害怕」這個主題,卻讓我頓時冷感。不,並不是說我感受到詩裡面呈現出的「害怕」感,使我覺得受到威脅,或是兔死狐悲傷其類,而是,我想能這麼樣寫出「害怕」,木焱這傢伙一定已找出超克(呵,最近在報上看到這個趣味怪字)「害怕」的出路了吧!一想到木焱已脫離「害怕」而能冷眼旁觀,就讓我對裡面的「頭髮」情慾感到很漠然。
8號詩「歲月啊有一根頭髮」是敗筆,這是我問木焱時他親口承認的,因為這實在有點老套。不過話說回來,這不一定是敗筆,說不定,這是絕妙的一筆。畢竟「妳嘴」一出現,「廁所」、「盥洗盆」、「杯子」也就猥褻而陰騭地沾染了「妳嘴」的意象,而「歲月」無疑是一種吞噬性的概念,這時候掉落下「一根頭髮」,就很有妙趣了。因為頭髮是歲月的象徵,除了對身體有保護作用外,也是決定身體外型美醜的一大關鍵,但是頭髮做為身體的一種排泄物,畢竟是要掉落、要剪除的東西,所以我會說,這時候掉落下「一根頭髮」,就很有妙趣了。最後,「被你們研究」讓我莞爾一笑。
木焱的詩集《No.》,怎麼說呢,就像自拍相簿吧。他在生活中的許多意想不到的情境,把攝影機藏在許多意想不到的角度,用各種意想不到的方式:瞬間攝影、曠時攝影、有色鏡片、特殊的閃光燈、偶而用即可拍等等,拍下了他自己的形象。總之,木焱就是木焱。想認識他的人,就去認識他。
木焱也想認識你。
參考資料:
木焱,《No.》,木焱詩集,(台北:撰者,2003)。
木焱,《秘密寫詩》,木焱詩集,(台北:撰者,[一版二刷]
2002)。
張錦忠,《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台北:麥田出版,2003)。
謝小鳯,《從社會語言學觀點探討馬來西亞英語之本土化》(The Nativization of Malaysian English:
A
Sociolinguistic Approach),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研究所碩士論文,(台北市:撰者,2002)。
王潤華,《華文後殖民文學》,(台北:文史哲出版社,2001)。
鄒嘉彥、游汝杰 編著,《漢語與華人社會》,(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
李志賢,《馬來西亞華文獨立中學歷史課本之分析(1975-1999)》,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南投縣:撰者,2001)。
陳大為、鍾怡雯主編,《赤道形聲》,(台北:萬卷樓,2000)。
陳大為,《亞洲中文現代詩的都市書寫1980-1999》,(台北:萬卷樓,2000)。
黃萬華,《新馬百年華文小說史》,(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9)。
饒芃子主編,《中國文學在東南亞》,(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1999)。
李如龍,《東南亞華人語言研究》,(北京:北京語言文化大學出版社,1999)。
商禽、焦桐主編,《八十七年詩選》,(台北:現代詩,1999)。
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台北:元尊文化,1998)。
莊鐘慶、莊明萱主編,《東南亞華文文學與中國現代文學》,(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1991)。
Tham, Hilary, Lane with No Name: Memoirs and Poems of a
Malaysian-Chinese
Girlhood, Boulder &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1996.
Tham, Hilary, Men & other strange myths, Colorado Springs:
Three Continents
Press, 1994.
Tham, Hilary, Tigerbone Wine, Washington, D.C.: Three Continents
Press, 1992.
柏楊 主編,《新加坡共和國華文文學選集(詩歌)》,(台北:時報出版公司,1982)。
轉載自Kama的文藝俱樂部
[ 點閱次數:13509 ]
存在一棵無花果樹──我讀黃遠雄詩集《等待一棵無花果樹》
說到底,在百孔千瘡和海市蜃樓的生活中,我們更需要的是時時喚醒自己:親愛的,沒有那樣的鳥蛋。 ──沙禽
去年杪返鄉,從南院馬華文學館處取得黃遠雄由雙福出版基金會贊助出版的新詩集打字稿,迅速翻讀後,腦海竟然沒有半點感想。在回台的飛行途中再次展讀,希望在字裡行間找著可以共鳴的意象,挖掘詩中的涵義,結果亦是徒然。
直到讀過張錦忠的序言〈與遠雄同行,繼續〉(星洲廣場,文藝春秋,2007/10/21)和沙禽的賞析〈歷練之歌〉(文藝春秋,2008/2/17),我雙雙對照手中文本,還是無法連接,破解詩文密碼,乃至於就在部落格說「黃遠雄的詩我很多都看不懂!」,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其中,yts(部落客ID)羅列了對黃遠雄近年來詩創作的見解,認為他的作品已大不如前,試摘錄如下:「他去除了意象表述,以語言直指現實生活的感知。因此他面對的問題不是在於寫甚麼,而是如何寫。……在直露的書寫中,往往必須靠語言去撐持,……,語言一旦撐持不住,不免就會讓整首詩垮蹋下來,而失去了詩的魅力。……左手人的詩寫得不錯,是因為他懂得營造氣氛,或狂飆式的氣魄,裡面含蘊著他強烈的情感,那彷如用語言撞擊語言,撞出了雄壯的聲響。那時期如「一棵不斷走動的樹」幾乎是名句,在七0年代而言不同凡響。然而,中年過後,他的語言找不到生命感了,生活磨去了他的那一份芒銳,卻同時磨掉了他在詩語言上的一股銳氣。這情況在李宗舜的詩創作上也同樣出現。是以,從左手人到黃遠雄,或從黃昏星到李宗舜,他們的創作都面對到同一個難題,即:詩語言轉化的失敗(?)或也可說,到了他這種年齡和心境,詩的技藝與語言已經無法撐起他的生命之重?一切的現實,只有生活。」(全文頗長恕未能盡錄,可上網參考http://www.got1mag.com/blogs/muyan.php/2008/02/24/asmcmaas_as_as_cbfec_er_e_ne_ecce#comments)
Yts的短評字字到位,論據可抵,以詩語言、意象和美學來切入,而據此拋出黃的詩的技藝與語言已經無法撐起他的生命之重這個問題。Yts可說是一位認真而且挑剔的讀者,他用了一把形而上高度的尺來衡量一名作者的生命歷程(但其實是過份的要求,敢問可以撐起生命之重的詩語言與技藝標準何在?詩人對待生活一定保持銳氣不可嗎?)。不過,如果你是一個愛詩人,請暫且收起任何成見,不要去管好與不好的問題,因為我終於讀出了不一樣的黃遠雄。
左手人或黃遠雄寫詩40年,至今只得3本詩集,當下付梓的即是黃遠雄一度停筆不寫後於1998重拾詩筆的結集。十年來,他只寫了一本詩集的詩作量?黃遠雄自己透露寫詩很慢,一首詩往往要琢磨好久。此番話想必是他近年寫詩的一種態度。當我們翻開這本詩集,很容易就讀到詩作中的「緩慢」,其中又帶著一種「不可承受之重」,這便是我幾番無法破解黃遠雄詩文密碼的原因。真要打開詩集的大門,第一必須卸下以往對詩歌解析的文學理論,第二必須放下對文字意象和尋找佳句的敏感(因為該本詩集幾乎直白),第三讀的時候必須慢,切勿急躁。如此,我們才領到入場卷,接下來就各自去開啟作者的幾十道(首)「書寫自我」的門窗。
我常以為詩人在詩中所追求的無非是不可企及的烏托邦,在文字中去完成他的想像,或者「作為自我救贖」(沙禽語)。直到遇見黃遠雄的「無花果樹」,我的思想碰到了沉重的門窗,推不開,到不了。黃遠雄在這堆文字作品裡向讀者顯露現實生活中的自我──那個赤裸裸的本性,幾乎就是存在主義大師海德格所說的本真了(由有形的存在者,認識無形的存有)。他毋須隱藏,毋須轉譯意象,毋須設計意境;他本身的現實經歷即是他對詩/詩人的存有的表徵。直接地說,他所處的世界,眼光所觸及的外界,就是他的詩界。因此他的書寫也無關乎詩與非詩,美學或非美學,他就是書寫的本身,他就是詩的本身(他即是本真的言說?!)。
讀者若以此思想去讀,就可以明瞭黃詩,例如〈文字同行〉中「漸行漸遠,我想起了‘湮沒’」,他在寫詩(存在者)亦在寫自我(存有),遂後這些文字「走過時間,走過我/相遇相知後/成了日夜/成了我們」,詩和自我已然結合成一個本真(On Being)。
再看〈寫詩與守夜的癟狗〉,此處黃遠雄藉外在正在寫詩的我去書寫自我變成一隻「癟皮的老狗」,「牠有意或無意的狂吠/正好劃破淤滯的時空/讓我抬眸」。在虛與實之間,那一句「牠有意或無意的狂吠」寓意了黃遠雄自我對生活處境的不滿,而他又能怎樣改變?他僅能寫詩,以詩去「面對一座巨大空無」。最後的兩句「回神/照見來時路」硬是把自我那份存有拉回現實,一切於焉休止,彷若沒有發生過。
釐清黃遠雄這本詩集的思想理路(希望如此而已)後,我們追蹤他在現實生活中的道德價值觀。從詩集裡可歸納出一組為數眾多的政治或社會詩,他時而針貶時事,時而嗤之以鼻,服膺的是對正義與平等社會的使命感。例如〈挑釁〉雖寫山水之景,實述暗潮洶湧的政治動亂,一句「一枚憤怒垣喋如我」便見立場;「一蹤一躍/就可以識破他偽裝的氣度/肺腑中狹隘的容量」,隱射的不就是鎂光燈下那些講大話的政客達官!黃不僅「撩起鬆垮的褲管/凝聚火力」(〈內巷〉)準備跟惡勢力拼鬥,亦見其處世之道的延意,如〈設立窗檻〉最末二段:「監視在被監視下如常進行/一切噪音行將止於智者/我循序跟進/無意包庇/踰越」,告示了讀者他對於強權的無懼,只是跟進了智者的舉措而已。如果讀者據此無限發想,誇大他的勇者無懼,他又有話說,因為「我只想、匆匆、趕路/回家」(〈趕路,回家〉)。
至此,我們不僅讀到感時憂弊的黃遠雄,也讀到邁入耳順之年的黃遠雄可愛又調皮的一面,和不認老的黃遠雄,仍想要有「急起直追的快感」(〈釋放〉)。
很抱歉的,黃遠雄的詩集我只讀完三分之一,剩餘文本背後的事件和故事並非我這個比他年輕26載的讀者可以馬上消化、體會,等待未來的遲來的共鳴吧(大概只有沙禽、張錦忠等同輩或接近其年代的讀者能馬上心領神會)。
如果有人因為讀畢此篇賞析而說這本詩集為存在主義的產品,我想我和黃遠雄都不會同意。他的詩作或許受到存在主義的影響,討論存在的問題,但其實意是討論現實中存在的本質,虛無(或者黃遠雄指的空無),以致我讀過的詩篇,沒有絲毫印象的殘留,因為虛無即是沒有。那些可寫可不寫的現實面,彷若沒有發生過,而黃遠雄受到「污染」後,硬是咳出來一口尋常不過的生活中的痰。
現在──套用海德格的詮釋,以「過去」的一切存有做基礎,以走向「未來」的存有做目標──我相信,我很快就能逐一讀懂、分析黃遠雄這口痰的虛無,以及它對一棵(或將來的更多棵)無花果樹成長的影響──他的等待轉變成對後世的影響。
黃遠雄,繼續在內心茁壯一棵,直指我心、你心,的無花果樹。
[ 點閱次數:11897 ]

格格不入
詩的最終是回報,詩的初始我忘記了。無國籍詩人來到地球找尋食物,逐漸消瘦中。
請用以下一項機制登入或註冊:
- » 使用Facebook帳號:
- » 使用有人部落帳號:

有人出版社于2003年成立于馬來西亞吉隆坡﹐由一班年輕的中文寫作者組成﹐目前以業余方式刻苦經營。其成員背景多元﹐來自廣告﹑資訊工藝﹑新聞媒體﹑出版﹑音樂﹑電影甚至投資界。有人虛實並行﹐除了經營網上"有人部落"﹐也專注藝文書籍的出版和製作。



